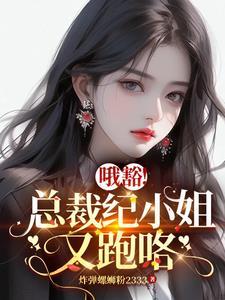车臣小说>高嵋山下是侬家翻译 > 第3章 欧阳夫人来归(第3页)
第3章 欧阳夫人来归(第3页)
不远处的小路上,曾麟书驾着马车,国藩坐在车上,从鸭群旁走过。
国藩几次抬眼偷看父亲,欲和爹说点什么,心里却像犯了什么大过,无颜面对。他捡起车上的一根稻草衔在嘴上。
他在纠结,帮婆婆买药是否自己的一时冲动,是否逞一时之侠义?可那时,真还容不得他多想,那是人性本能的驱动。如果,他不这么做,这辈子他都良心难安。可自己的药还是家里卖的稻米。他将稻草咬断又吐出,轻轻叫了声爹。
前面赶车的曾麟书,闻听儿子在叫自己,手耷拉着鞭子,喃喃道:“有时候,大人的心思,你可能不完全明白。”
国藩越加纠结和痛苦:“我何尝不知家里处境,只是,那婆婆太可怜了。”
曾麟书面无表情地叹了口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我们读圣贤书,就是要做圣贤之人。你做得很对,不必为此纠结。”
国藩惭愧地说:“孩儿没能力帮助家人,反让家里为我寻医问药。”
曾麟书回头对儿子道:“读好你的书,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可,孩儿见爹一脸的不开心。”
“爹不是因你送别人药,爹是在想,爹活到今日反倒不如自己儿子。当你表示要为那婆婆买药时,其实,爹也在思量。只是,你赶在了爹的前面。今天,那几副药,或能救回两条性命,甚至是一家人。”
国藩将手中稻草狠狠投在路边:“唉,心好痛。”
曾麟书问:“为那婆婆,还是为我们家?”
“都有。”
曾麟书缓了缓道:“你也别太往心里去。明天,我们家学馆,又要开蒙拜师了。也会收到些银两补贴家用。另外,我想让,”
国藩没等爹把话说完:“爹,这段日子,我会帮您教授学生,爷爷与我谈起过此事。”
国藩短短的一句话,曾麟书顿时像充足了电,只见他精神一振,朝马挥了一鞭,‘驾’的一声,马儿奔跑了起来。
夜幕如期降临,织房传来有节奏的织布声。这是奶奶带着国芝和国蕙又开始了夜间的劳作。
随着砂锅升腾的热气,整个厨房弥漫着浓郁的草药味。母亲江氏用抹布裹着锅把,国藩忙拿出两只碗放在案板上,江氏将药徐徐倒进碗里,回手将药渣倒进一只铜盆里,她拎起水壶往盆里倒些热水,对儿子道:“端进房,先泡腿吧。”
国藩端起药盆走出厨房,江氏随后端着药碗,一起来到国藩屋。
国藩脱去鞋袜,将脚泡进盆里,母亲蹲下为国藩拉裤腿,国藩忙说:“娘,您别蹲着,我自己来。”
母亲坚持半蹲着为国藩洗腿:“唉,赶紧好吧,娘若能替你,娘早替了!”
国藩望着有孕的母亲和她那不再乌黑的头,不由一阵心酸,江氏仰头看看国藩:“嗨,喝完药病就好了,不要总把病压在心上,谁没个病的灾的?有病,咱治就是了。”
母亲佯装轻松,安慰着儿子,国藩却带着哭腔:“我的病算什么,看把您给熬的,头都白完了。”
母亲苦笑了下:“人老了都会有白的。行了,你多泡泡。”她回身端起桌上的药,“嗯,可以喝了。”
国藩接过药一饮而尽,母亲接过碗叮嘱着:“水凉了就不要再泡,脚底下都是穴位,受凉了不好。”
国藩哽咽地朝母亲点点头。
“今晚早点睡,熬夜对病更没益处。行了,我去服侍奶奶睡觉。”母亲话毕出了屋,国藩见娘出了门,捂着嘴暗自流起泪来。
突然,小国荃推门进来,怀中依然夹个小褥子,国藩见状忙说:“怎么又是你。”
国荃见大哥红着眼,胆怯地:“这次,不是偷偷来的,娘允许的。”
国藩看着稚气的九弟,心中五味杂陈。他张开臂膀:“来!大哥抱抱。”
国荃将褥子往床上一丢,扑向哥哥怀里。国藩慈父般地紧紧搂着九弟,眼泪簌簌而下。他恨自己不能为家分忧,反倒被一家老小关爱着,那种愧痛,比身上的癣疾更加折磨。
国荃依偎在国藩怀里,见大哥在掉泪,他想安慰却不知说什么,他伸出小手为大哥拭着泪:“大哥,白天,我随爷爷到祠堂开会了。”“哦,是吗?”
“是的,我代表全家参加的会议。”
“九弟可以做全家代表了,你好了不起也!开会都说了什么?”
“嗯,说是要写什么谱。”
“家谱?”
“对,大家说要重新写家谱,还要修缮祠堂。哥哥,家谱是什么?”
“家谱就是,啊,你先躺床上,大哥把水倒掉,等下,我们躺在床上大哥和你讲家谱的事。”
国藩将国荃鞋子脱掉,国荃爬上了床,国藩擦干脚端着水盆出了门……
新一天的太阳尚未爬上树梢,全家的早餐已经结束。
国蕙和母亲收拾完餐厅的碗筷朝厨房走着,国芝从客房端着放有两套礼服的托盘,恰好走来。国芝看着娘手上的饭碗:“娘,您厨房放着,等下我洗。”
母亲看眼国芝托的衣服,“赶紧得让大哥他们穿好,爹和爷爷屋里等着呢。”
母亲边进厨房,边自语着:“哈,这小东西,什么都少不了他。”国蕙接话道,“让九弟跟着去吧,见识下学堂的规矩也是好的。”
母亲顿了顿神:“爹原打算,待九弟五岁再让他正规读书。”
国蕙说:“九弟比人家六岁的孩子点子还多,早些开蒙早些中秀才。”母亲不觉一乐,“哈,但愿吧。”
国藩在房间为国荃穿礼服,国芝端着托盘一旁站着,国藩回头一笑:“哈,瞧你,丫鬟似的站着,放桌上吧。”
“那你们快点,爹和爷爷都等着呢。”国芝放下托盘,“大哥的礼服在这里,不管了哈。”她说着跑出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