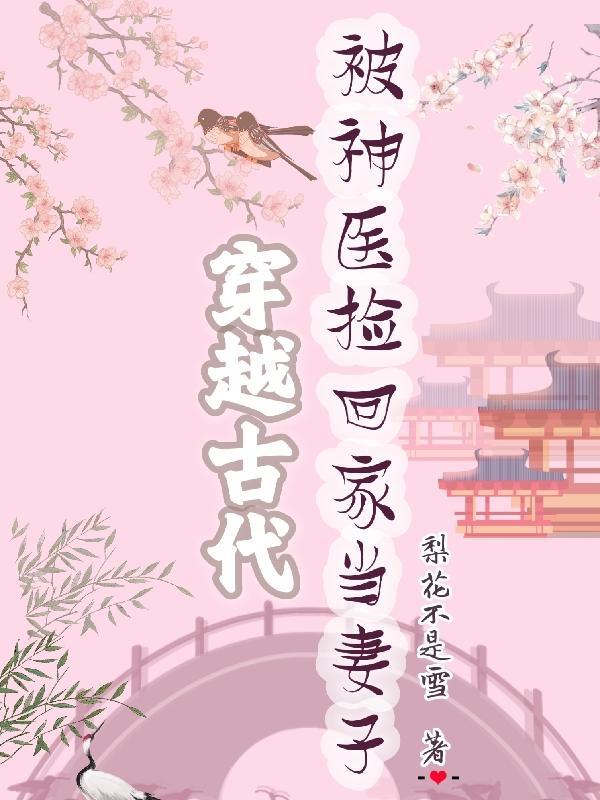车臣小说>我这一生 如屡薄冰 > 第402章 皇祖母何意(第2页)
第402章 皇祖母何意(第2页)
莫名其妙的表明自己的论述切入点,刘荣便丢出了自己的问题。
“世人皆知,太祖高皇帝戎马半生;”
“自打举反秦义军于丰沛,之后不是在抗秦,就是在讨伐异姓诸侯不臣。”
“为了在当初,我汉家府库空虚、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凑够讨伐异姓诸侯的军费,太祖高皇帝,可是连三铢铅荚钱这等手段,都不得已使出来了。”
“——皇祖母认为,这是为何?”
“何以太祖高皇帝,如此不信任后世之君——如此不信任孝惠皇帝,宁愿在战场上厮杀至死,也不愿将哪怕一两家异姓诸侯,留给后世之君去处理呢?”
…
“是太祖高皇帝,自负到认为后世子孙万代,都出不了第二个能动异姓诸侯的明君?”
“是孝惠皇帝,当真昏聩无能到以天子之身,都对付不了一两家异姓诸侯——如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之类?”
“退一步讲,就算孝惠皇帝果真那般软弱无能,太祖高皇帝当真那般瞧不上孝惠皇帝,不也还有吕太后吗?”
“莫非吕太后,也办不成这件事、也除不尽我汉家的异姓诸侯?”
“又或者,是太祖高皇帝好大喜功,不愿将哪怕一丁点功勋,留给后世子孙去安身立命,非得把伐灭异姓诸侯的功劳全都占了?”
“若果真如此,太祖高皇帝又为何带头‘自污’,极度否定自己英明神武,反而去强调虚无缥缈的君权神授?”
“好大喜功的人,怎可能受得了如此委屈?”
“受得了如此委屈的,又如何会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呢?”
如机关枪般,突突突突一连串的问题,问的老太后多少有点懵。
也就是那么片刻呆愣,让老太后下意识脱口而出:“自然不是。”
“太祖高皇帝,自然是个明君。”
“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出于宗庙、社稷之考量。”
“故而……”
“故而………”
话说一半,老太后终于反应过来,刘荣究竟要说什么了。
只是话头已经开启,偏偏老太后还接了一下、拖了一手。
这一下,刘荣可就没法打住了。
“皇祖母心里明白。”
“孙儿,也了然于胸。”
“——太祖高皇帝,既不是好大喜功,也不是对后世之君无差别蔑视。”
“而是太祖高皇帝明白:异姓诸侯之弊,每拖一天,便会多出一份险阻。”
“若拖得够久,便是英明神武如太祖高皇帝、‘功高莫过于太祖高皇帝’的开国之君,也未必就能奈何的了雄踞关东,并逐步强盛的异姓诸侯。”
…
“所以,太祖高皇帝,宁愿拼上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也要为后世之君,彻底扫清异姓诸侯之弊。”
“即便这么做,让太祖高皇帝为汉王五年、位九五七年,却几乎不曾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甚至于连性命,都丢在了讨伐九江王英布之后,太祖高皇帝,也仍旧在所不辞。”
“——孙儿尝闻: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太祖高皇帝手段尽出,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伐灭异姓诸侯,不过是为我汉家——为孙儿在内的历代先皇、后世之君,而‘计深远’而已。”
“便是民间凡夫俗子,尚且会有苦一苦自己,攒下积蓄给后代换前程的念头;”
“何况是我汉家的太祖高皇帝——何况,是我汉家的县官、天子呢?”
如是一番话说出口,刘荣即便还没真正去做这件事,也已经莫名感觉到自豪了。
——最后一句话,刘荣说的不仅是‘何况是太祖高皇帝’,而是稍带上了‘汉天子’三个字。
很显然,老太后听出来了刘荣这层意图。
只是理智回归后,老太后的重点,仍旧放在吕太后这个史诗级副本的地狱难度之上。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帝王之爱民,则筹谋以图安。”
“——安。”
“国有强有弱,时强时弱,然亘古不变者,不外乎‘安’字而已。”
“皇帝之所欲,乃欲强国。”
“强国,有很多办法。”
“但触碰吕太后,会使宗庙不宁、社稷不安。”
“相较于这‘不安’,皇帝所谓强国——所谓‘为后世之君计深远’,也不外乎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