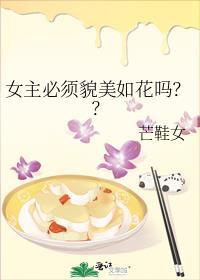车臣小说>恋人成了痴情男二 > 第92章 借酒浇愁(第2页)
第92章 借酒浇愁(第2页)
听见兄长的训斥,他一句也未曾反驳,只是自嘲一笑,“她又不在乎。”
“……”
那就是真吵架了。
江在洲实在想不明白自家弟弟是做了什么天愤人怨的事,竟然会惹得谢枝同他吵起来。
毕竟谢枝是那样软的性子。
“吵架了就去把话说开,来我这里饮酒做甚。”江在洲拉人起来,“我瞧着谢枝也不是什么不冷静的性子,你同她好好说,她还能故意寻你的错处不理你不成?”
江上影被拉得起身,临到门前却又转身去拿自己的酒壶。江在洲阻拦不及,竟又让这小子一饮而尽。
江在洲拿着空空的酒壶无语凝噎。
江上影饮完了最后一壶酒,跌跌撞撞地又往回走,跌坐在椅子上。
“兄长……”江上影靠着椅背,头往后仰,一手捂住眼睛,哑声道:“谢枝不是真心嫁我,她有喜欢的人,那人会替她梳,会为她做吃的……”
江在洲皱眉。
也许是酒意蒙蒙上头,他才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面对这个事实。
他喉结滚动,轻声道:“在谢枝心中,我与他,犹如尘埃与星辰,处处皆不可比。”
上了床睡意却一下子都没了。
谢枝翻来覆去,数了几百只羊后还是睡不着。
她猛地坐起,静静地看着身侧那泛凉的枕头,少顷,她掀开被子下床。随便套了双靴子就推门出去。
此时夜已经深了,雨不知何时在谢枝没注意的时候就停了。雨后的夜晚天幕比平常都漆黑不少,渐渐的,竟缓缓爬上了几颗星星。
谢枝缩了缩肩膀,裸露的脖子上泛起星星点点的鸡皮疙瘩。
出来时没想太多,竟忘记带一件外衫了。
这么一会儿,她早就走出了好大一段。
想也不想,谢枝就默默否决了回去披件外衫的决定。
白日里,江上影知道她有轻微路痴的毛病,特意带她走了好几遍军营,还带她认了个别人的营帐。
如今也还没过十二个时辰,她还是记得路的。便循着记忆里的路线走去。
漠北军营大,营帐与营帐之间也相隔甚远。因着当初谢枝说要远离校场的要求,江上影和她住的屋子就坐落在军营的最边角。而她要去的江在洲的营帐则是在军营的正中偏西。可谓是大半个对角线,距离也是十分远。
谢枝走着走着觉得这军营内简直静的吓人。
但其实夜里巡营的守卫不算少,只不过谢枝走的巧,竟一次也没遇上。
下了雨,路走起来便十分泥泞,而这泥路走起来的唯一好处就是——它会放大每一个人脚步声。
所以在那脚步声接近自己时,谢枝几乎是瞬间躲开了。
好巧不巧,她跌进了一个死角,迎面就是那看不清脸的人,唯独他身上那身锃亮的盔甲让谢枝清楚地知道他是漠北军中的将士。
“营里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娇软的姑娘?”那人狞笑着朝谢枝逼近,“是来给爷解闷吗?躲什么啊,来爷怀中,爷会好好疼你的。”
谢枝往后退。
恰好此时火光一闪,双方均看清了对方的脸。熟悉的令人恐惧的面孔从心底清尘显像,瞬间,谢枝瞳孔骤缩,立马要放声大喊。
却又被那人迅地捂住嘴,砰得一下将她按在泥地里。
巡营的人闻声停住脚步,转身朝这边走来,“是谁在那儿?”
谢枝呜呜挣扎。
那人眸中似是兴奋又似是癫狂地用另一只手掐住谢枝的脖颈,力道之大,让谢枝的挣扎都弱了许多。
那人压住自喉中涌上的粗重喘息,而后平静地朗声回应道,“刘哥,是我,张究。”
两人似乎是认识,巡营的人停下:“你在那儿干嘛?”
张究语气故作羞愧地答道:“害,这不是摔了一跤嘛,你别过来了,忒丢人了。”
被叫做刘哥的人哈哈笑了两声,打趣道:“都叫你别总是去春风阁了,看吧,路都走不稳当。”他转身边走边道:“不严重的话明日可别误了操练的时辰。”
“欸!”
巡营的人走远了,张究才低头看被自己压在地上的女子。
他有把握力道,能叫人不至于窒息死亡却也无力挣扎。
所以,在放开手的时候,谢枝也只是因为缺氧而头脑昏沉全身无力,并未直接晕过去。
“我是不是见过你?”张究嘴角扯了个笑,眸中是让人作呕的欲望,“听说江二公子带了他的夫人进军营,你不会就是那位夫人吧?”
“……”
谢枝被捂住嘴说不了话,只能惶恐不安地瞪着张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