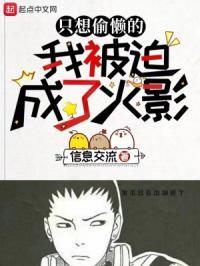车臣小说>被命运抛弃什么意思 > 第177章 看长远些(第1页)
第177章 看长远些(第1页)
我拿起手机一看,却是我的父亲张明德。
这些年,父母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的,弟弟呢干脆就从没给我打过电话。
家里人可以说几乎从不给我主动打电话,可能他们脑子里就没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我打过去。但这几年我也很少打了,我一个人既带孩子又上班,我也很累,我带着春妮独自硬撑着过了十年,他们没有过问过我一句,没有关心过我一句,致使我在无数个黑暗的夜里,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苦苦挣扎之感,我过得越艰难就越心灰意冷,慢慢地我也懒得给他们打电话了。
由过去的一周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变成几个月一次。。。
最近的几个月都没有打过电话。
张明德突然给我打微信视频电话会是什么事呢?
不管什么事,我都有点心虚,不敢接。
屋里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大胖儿子,视频被他们看到了他们会怎么说呢?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件事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惊涛骇浪,尽管其实我的生活跟他们没有一点毛关系。
先这在他们看来是丢脸至极的伤风败俗的事,当年我跟王晓峰领了结婚证,还未举行婚礼,因为婚礼得回老家去办,那得等到我暑假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年轻,两个年轻人一冲动觉得反正结婚证已经领了,怀孕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当结婚前一天沈秀兰知道我怀孕了的事后,不是关心我身体怎么样,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丢人死了”!
如今我居然又一次旧错重犯,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无可救药。
然后就是对于我自己傻乎乎的独自承担养这么一个大胖儿子,而不去跟男方追究责任,我是傻透了,脑子肯定进水了。
沈秀兰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不肯吃亏,除了她的娘家人和她的宝贝儿子,再其他人跟她打交道,总要放在秤上称来称去,如果哪件事让自己吃了亏,会挂在嘴上说个三年五载,不依不饶,没完没了。
如果冬青的事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毫不客气地卷入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三番五次的搅扰地我跟孩子们没有安宁的日子。
我性格并不是那种什么事都要跟人计较的人,对我来说,打不起交道的人,我不会去纠缠,远离就可以了。
他们鸡飞狗跳的过了一辈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从小在那个家里长大,看着他们那样的生活我实在是厌烦至极,那么多年考验我的忍耐力到了极限。
他们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并无任何智慧,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自内心地不想让他们掺和我跟别人的这些恩怨是非中。他们的参与,只会让事情变成一团浆糊而已。
我是四十岁的成年人了,我的事该怎么处理,我有自由,也有自己的方式。
我一直没有接张明德的视频电话,铃声很顽强的响了一会儿后终于停歇了。
我需要好好想想,理一下我的生活现状,要想好了该跟他们说些什么,而不该说什么。
说起来,我辞职的事,也还没跟他们说呢,如果说了,他们肯定也是各种埋怨,各种替我可惜。在他们极其有限的视野和认知里,我以前的工作——大学老师,就是这世上再好不过的工作了,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份差事更好的了。如果我辞掉了这么好的工作,以后我就有的苦吃了。
果真是这样吗?
偏偏我就不信邪。
如果以后真的要吃苦了,那我也不后悔,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即便最坏的结果,我也要自己承担。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即便是父母也不行。
半小时后,我主动给父亲张明德去了一个电话,他很快接通,我说“爸,在干嘛呢?”
张明德在那边以一贯的生硬说道“今天下雨,在家待着呢。”
张明德虽然当了一辈子老师,还当过十年的小学校长,但他的嘴巴很笨,说话非常可笑。
记得我买房子那年,弟弟张磊也在要在那一年买房结婚,那时候我已经跟王晓峰离婚,我自己的钱不够,父亲张明德在母亲的主张下把他的钱六十多万全部给了张磊。
当然我也没有指望他们能资助我。
我厚着脸皮抱着碰运气试试看的态度跟单位借钱,没想到老领导一口答应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里,父亲说“哎呀,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嘛。”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弟弟张磊呢,听说我有了这样一笔钱,打的主意则是,能不能先挪给他用,按他当时的话说“他买房是刚需啊”!
我也没有房子,也是租房住,但没人觉得我需要买房,没有考虑我的刚需问题。
那时懦弱自卑的我,第一次体味到来自我那个原生家庭的凉薄。
尽管如此,此后的几年里,我依然给他们买吃的,买穿的,买生活用品,买厨房电器,就想着改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
后来,我离婚了,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回家,千里迢迢坐火车二十多小时,回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现烧。待两天惹得母亲不高兴时,她会直接说“这些畜生东西,还不如不要来了。”
这些话就像初冬的冷雨,无情地浇到我身体,深入我的肌肤,令人久久难以忘记。
后来我带着孩子在滨都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也没有能力再给他们买什么东西,我不跟他们联系时,他们不跟我有任何主动的联系,尤其是我的母亲沈秀兰,她就像没我这个女儿一样。
我的心就这么一点点地冷了下来。
一个家庭,一个当妈的,把最善良最老实的那个孩子逼得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榨干了这个老实孩子的价值后就不理不睬,我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除了在夜深人静时叹息自己命运太差,投胎的技术太差,还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