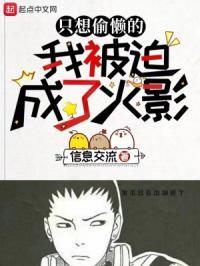车臣小说>被命运厚待是什么意思是 > 第173章 努力活着(第1页)
第173章 努力活着(第1页)
我像什么也没生过那样,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春日信使”酒吧。
我尽量低调,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另一方面,我一边干活一边又时刻支棱着耳朵,想着会不会有昨晚18号包房”那个客人”的后续情况,毕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可是直到晚上快要下班时,也没有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听到关于他的只字片语。
这里,就像是一个人潮的中转站,人们来这里获得片刻灵魂的放纵或肉体的麻醉,尔后又向着各自的方向散去。谁也不会关心某个陌生的人来自哪里去往哪里。
这样也好,这是我最想要的结果,希望昨晚只是一种巧遇,我们各自相安无事。
这样,几天之后,关于18号包房的那点小插曲就会被繁杂的生活琐事厚厚的覆盖,将会被我彻底的遗忘。
这一天整个下午至晚上,张姐也始终没有露面,她很少有这样不在场的情况,一直以来她可是这家酒吧的定海神针啊。但今晚她不在,似乎一切也都没有乱套,都在像往日那样闹哄哄地运转着。果然就是应了那句话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
不管那么多了,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儿子冬青像往常那样欢快地迎上来,紧紧地扑进我的怀里,头在我的胸前蹭来蹭去地拱着。
实话说,在冬青出生之前的无数个夜晚,我都想过,纠结过,到底要不要将他生下来?如果生下来,他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会不会怨我呢?
我承认于内我是懦弱的,我不太敢做人流,我这半生也从来没有做过人流。害怕疼痛,害怕对身体的伤害。于外来说我又是内心柔软的,再三思虑也不忍心将一个无辜的生命轻易的扼杀掉。
我爱孩子,只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非常可怜的孩子。
我要好好爱自己的孩子,尽我所能地去爱他们。把我没有得到的都给她们。
最后终于坚定地选择了生下他。至于其他可能会遇见的现实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就这样,一个粉嫩可爱的小天使来到了我的身边。
当然这件事,从头至现在,张明德和沈秀兰都不知道。
不能让他们知道啊,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就是重磅炸弹,他们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震惊成什么样子,会愤怒成什么样子,会把我骂成什么样子,那个场面我完全无法想象。
可话又说回来,我的生活又不靠他们——靠也靠不上啊,我一个人带着春妮过了这么些年,沈秀兰过问过一句“你一个人带着孩子都是怎么过的啊?”没有,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更没有任何想要帮帮我的话。张明德什么都顺着老婆,一切以老婆的想法马是瞻,自然也跟我这个落魄失败的女儿保持着清晰的“楚河汉界”。他们就是这样的父母,当你过的好,过的风光时,他们就关心你,当你过的失败时,他们会很讨厌你,一种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驱使着他们疏远你。
既然我的生活已经跟他们无关了,那么我的任何事,也都没必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没有必要给自己引来额外的烦恼,没有必要让他们把我简单宁静的生活搅扰的一团糟。
而且我也不想让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父母,一切事情的决定因素先是自己的面子,是别人怎么看。在乎外人胜过在乎自己的孩子。
我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母亲,爱惜生命,尊重孩子。
就这样,冬青这个既不幸又很幸运的小家伙降生了。
冬青的到来,真是像上天赐给我的又一个礼物一样,让我感到幸福甜蜜,内心充实。
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负担,带着孩子陪他们一起成长的过程,我的心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净化,变得非常简单,非常纯粹,孩子们帮我治愈了过去留在心里的很多创伤,我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健康的人。我不再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而郁郁不平。被人爱固然幸运,可爱别人却更为幸福。
再苦再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在春日信使酒吧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上着班。
转眼一个月过去,到了跟医生约好的冬青该做手术的日子,这天我提前跟经理请好了假,带着孩子和一些简单的护理用品来到了医院儿科。
赵雪梅送完俩孩子上学,又处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务事,随后也来到医院陪我们。
在医生的安排下,冬青手术前做了一系列流程性的检查和化验,随着时间的推进,各种结果和数据都出来了,显示手术可以做,手术被安排在下午两点,终于来到了那揪心的一刻。
我在手术室外焦灼不安地等待着,赵雪梅陪坐在一旁,不间歇地安慰着我,三个小时过去了,四周还是一片寂静,这儿恐怕是这家医院最安静的地方吧?
雪梅得接孩子去了,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有人接放学,需要有人做饭呢。我们这两个苦命的女人,是多好的一对战友啊!
我继续在手术室外等着,暮色逐渐暗下来,街上的显得格外明亮,手术已经做了快四个小时了。
我知道,凡事都有意外,假如出现了最不希望的那种意外,我又该怎么办呢?我能扛得住吗?
不敢想,真是不敢细想。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手术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护士走出来说“你是孩子妈妈吧?”
此刻整个楼道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忙不迭的点着头说“是我,我是冬青的妈妈。”
“手术很成功。”
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生活中有太多的事,就像开盲盒,你根本不知道,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嫁人是这样,小升初摇号是这样,冬青的手术也是这样。
好在这一次上天眷顾,手术成功了!
没容我多想,冬青已经被几个医生护士簇拥着推出来了,麻药劲儿还没过,孩子还在昏睡中,随即又被送入了重症监护病房。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算是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