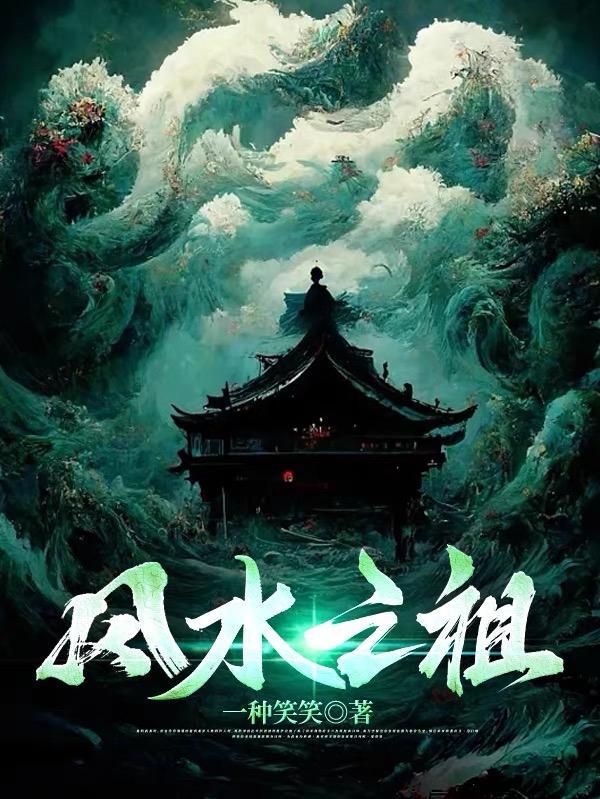车臣小说>救赎对象错成了反派 > 第2頁(第1页)
第2頁(第1页)
他用力捶向方向盤,指關節泛著白,腦子的線團一下子理清似的,他方向盤右打,油門踩死。
「您的導航小雪提示,此次目的地為漢京市人民醫院,路上擁擠,請小心駕駛。」
黑色卡宴如一道奔馳閃電衝了出去。
春歸和沈雪遲在一起五年,對於男人會死這件事,他早有預感。
可是他對沈雪遲有太多放心不下,所以就連死都牽掛著對方黃泉路上一個人怕不怕。
通向死亡的道路多孤單啊,那人不活,總該帶上自己。
漢京市人民醫院從一樓就被濃郁的消毒水味籠罩,春歸是個不到萬不得已不肯來醫院的人,可為了沈雪遲,這五年來他跑醫院的次數不下四百趟。
抑鬱症這種東西孰輕孰重,在遇見沈雪遲之前,他也沒想過這個病會要兩條人命。
聽說沈雪遲是張開雙臂前仰倒下去的,就像擁抱太陽那樣,可春歸依稀記得,這是自己最愛跟他撒嬌的姿勢。
青定決心,如果對方還能活,他一定要揪著男人的耳朵,大罵你他媽的真沒良心,誰家好人睡一覺就丟失五年相愛的記憶還要搞自殺啊。
但沈雪遲還是沒給他這個機會。
不記得在icu外面等了多久,只是太陽升起落下,春歸又冒出的胡茬,裡面的醫生跳交際舞似的跑進跑出,可無一例外的是每個人看見他都會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隨後無奈搖頭走開。
終於在第三天的晚上,其中一個主刀醫生走到他的面前,摘下口罩誠懇道:「進去看看吧。」
春歸呆滯地盯著醫生,一時間沒有動彈,恐怕下一秒他也要被推進icu了,不然他怎麼覺得自己的塑料心臟輕飄飄的,靈魂都出離軀殼。
直到很多年後,青年再次回想這一天,給出的評價依然是「不如死了痛快」。
那種感覺就像千斤重的石頭壓在他身上,從指尖泛起的麻意由上到下,從腳到頭,每走一步都是一千根針刺向他。
等他忍著劇痛終於挪到沈雪遲的床前時,男人還閉著眼,身上被包紮得嚴絲合縫,虛弱蒼白得像一片紙,氧氣罩隨著他的呼吸變白、透明。
春歸低頭靜靜地看著他,突然產生一種把氧氣罩綁在他臉上的暴躁想法。
似乎只要不取下來,沈雪遲就能一直活著。
早知道一開始就不同意什麼扯淡的自由,強行把人關在家裡,鎖在床上。
青年深呼吸一口氣,強打起精神,想用笑容面對沈雪遲,轉過身的剎那眼淚卻最先湧出來,他對上病床上男人漆黑如墨的眼睛。
沈雪遲醒了。
正在對他笑。
春歸的人生字典里在遇見沈雪遲後才添上了手足無措這個詞,這時他正手足無措地想要摸摸對方,但發現沈雪遲全身上下沒一處是能摸的,只好改變方向提起床頭的水果籃子。
他說:「沈雪遲,你再撐個幾天行不行?我不喜歡吃水果,你要是走了,爛了就浪費了。」
沈雪遲不說話,只虛弱地看著他笑。
氧氣罩遮住了他大半張臉,但春歸知道他的笑容是何種模樣。
永遠是一副溫吞的,嘴角微微彎到十五度。睫毛濃密又長,還生了對多情狐狸眼,眼尾上揚,偏偏他的眼睛裡裝不下任何人,但仔細湊近瞧,裡面還是有春歸的。
沈雪遲的食指輕輕抬了抬,這已經用盡了他全身的氣力,因為他的食指很快垂下去,了無生機地砸在白色床單上。
春歸看著,卻發出一聲哼笑。
看吧,沈雪遲,你就算不記得他了,身體還是會出自本能做出只有他們知曉的小暗號。
但男人只是繼續看著他,在氧氣機白氣消失的剎那,張口無聲說了三個字。
「不吃了。」
「哦。」春歸迅低下頭,用食指在地板上畫小圈圈,不愧是大醫院,地板擦得這麼幹淨,一點灰塵都沒有。
「你不出聲,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狡辯道。
沈雪遲無奈地彎了眼睛,他很困,眼睛閉上的頻率比剛才更多了。
春歸連忙拿起手機打開相冊,找出鹿可燃家出生的小狗崽。
這是一年前的事,他不確定沈雪遲記不記得,但隨便什麼,能和他多說說話就夠了。
「沈雪遲,你看這是剛出生的小狗崽,等你好起來,我們就去領養一隻好不好?你叫雪遲,那我們就叫它雪來,讓它早點來。」
沈雪遲睜開眼,靜靜地聽著。
他長得太好看了,任誰見了都得說一句美人,這幾年得病了,就是病美人,但唯一一個敢這樣稱呼他的,已經被春歸揍進了醫院落下終身殘疾。
當年他和沈雪遲剛在一起時,朋友們都以為他是鬼迷心竅,成了被妲己勾心的紂王,而沈雪遲呢,貧苦書生一個,肯定是為了錢才和他在一起。
畢竟這圈子裡有個公認的說法,春歸除了錢和顏值,一無所有。
春歸聽了不氣,反而覺得開心。
幸好他有很多錢,還有張好看的臉,這不得把沈雪遲栓他身邊一輩子。
但沈雪遲可能是個注重內在的傢伙,他肚子裡沒有墨水,所以留不住人。
……可惡,下輩子他一定飽讀詩書。
整整一個小時,都是沈雪遲在聽他講話,春歸恨不得扒開這人的眼睛,叫他別閉上,他每一次閉眼,青年的心都要驟停一次,說話的度不由得急上幾分,最後沒忍住帶了絲哭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