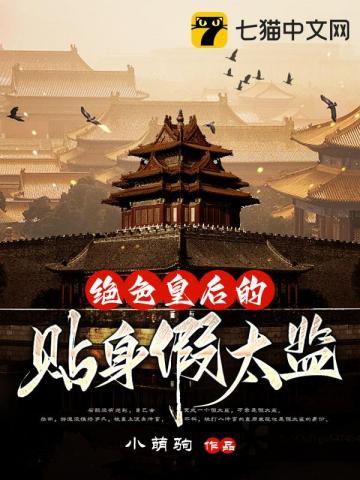车臣小说>公子壮 百科 > 第71章 生病(第2页)
第71章 生病(第2页)
何子鱼没吭声,赵玠也不多言。
床上人的呼吸渐渐绵长。
半夜何子鱼冻得直瑟缩,眼皮打颤,他悄咪咪摸到赵玠床边,轻手轻脚的坐上去,靠着床柱打盹。
这床也是那种暖炕,热流缓缓将他身上的寒气消解。他盹着盹着就陷进了温柔乡,好像又梦回当年锦衣玉食的日子一般。
次日他四仰八叉的从赵玠被子里醒来,缓了五息才回过神来,惊恐万状的窜下床。赵玠人已经不在了。
何子鱼心头咯噔一声:完了。
他第一天干活,就消极怠工,爬了东家的床。
也不知道身体里这个做了什么,对方颇为悠哉的道:“好睡。”
何子鱼紧紧抿住嘴,怕别人看到他这自言自语的场景。赵玠去了书房,他捧着手爪子兀自思索片刻,就打算装没那回事,麻溜的抹了把脸,溜出门去。
到院子里时赵玠正跟四叔聊昨晚的刺客,听到脚步声,两人齐齐回头。何子鱼忍不住头皮紧,猛的朝两人一躬身,把四叔吓了一跳。
赵玠神色平淡的朝他一点头,没责骂他,他怀揣着侥幸的心快步窜回家,路上遇到聂安,聂安笑问他昨晚如何,他支吾着交代了遇到刺客的事,把自己被追着跑这段掐掉。
聂安对他的武力一百万个放心,见他不负所望,一直到药庄都还在幸福地微笑。
何子鱼摸回家协助云娘熬好药,备好热水,等聂乌泡完药浴后他抱着小毛在娘身边撒了会儿娇,云娘觉得他虽然丑了些,但撒娇时奶里奶气的,竟有些可爱。
她失笑道:“熬了一夜,快去睡了吧。”
何子鱼捡回点睡意,摸去自己屋里睡到日上中天,雪化了,他裹着被子站在门口看云娘扫雪。云娘一回头,见他跟条虫似的杵着,直把被子拖到了地上,登时牙疼。
“把被子放下,弄脏了我可不给你洗,加钱都没用!”
何子鱼吸了吸鼻子,小心把被子放回去,精神抖擞的混到晚上,跟聂安交了班后,他被赵玠吩咐去房顶上守夜,冷风吹得他不住的吸溜鼻涕。
他不知不觉间就得了一场风寒,赵玠听他在房顶上哼哼唧唧的,叫人把他换下来。
何子鱼进屋被暖气一烘,没来由精神萎靡起来,这番他就病下去了,赵玠将他提溜到小塌上,叫人给他熬了碗药,药里放了糖,他头昏眼花的把药喝下去后,就摸着肚皮吧唧嘴。
赵玠忍不住想笑:“这样你怎么保护我?”
何子鱼飘忽的焦距慢慢聚拢:坏了,他昨晚睡了人家的床,今晚人家照顾他,这个侍卫的日子过得跟太爷似的,说得过去么?
何子鱼垂病中惊坐起,赵玠拿手掌按在他额头上,将他推回去。
温热掌心带着股熟悉的淡淡干香,他恍然失神。
“休息吧,以后好好为我出力,知道了么?”
舒缓的声音在耳畔回响,他点了点头。
那人走了,他偏头望着对方的身影,不自觉道:“方逊——”
颀长身影蓦地定住,缓缓侧过小半张脸,没回答他,走到灯烛前时将烛火吹灭。屋中一片黑暗。
他眼底蓦然热,回过神来后想起方逊已经被沉入弱水了。他抬肘盖在眼眶上,嘴角勾出一个酸涩的弧度。
坐到床上的赵玠微眯起眼,自知道何子鱼的身份后他就派人把那些有可能暴露对方身份的线索通通抹掉,让身处常州的司马峥无从下手,同时他还把这人的各种往事、习性、爱好全部搜到手。
他知道这人心上放着一个方逊,也知道这人跟司马峥有剪不断的爱恨情仇。司马峥罪孽深重再没翻身的可能,但他效仿着方逊的点点滴滴,仅只是用了同一种熏香,就让这人失了魂。
赵玠把手枕在脑袋下,听着对方出的细微动静。
一夜过去,何子鱼烧了,因为昨晚给他喝的药只是糖水加甘草红枣,他烧得昏迷不醒,聂安想把他带回去,被赵玠推掉了。
“庄子里有的是药和大夫,这里人手也足,有你看着,叫他待在这也不妨。”
聂安心眼够多了,但愣是没从少东家平淡的语气和冷静的表情立咂摸出半点不纯,他思索片刻觉得这话也对,就让何子鱼继续躺在庄子里。
赵玠差人来替何子鱼看病,这些人都是少东家的忠实狗腿,提前就被少东家招呼过了,所以何子鱼这风寒,好得就一波三折的慢。
詹屏将近十天都没看到何子鱼,守在他家门口等聂安回来,聂安一脸疲惫的走到门口,瞥了詹屏一眼,詹屏抿了抿嘴:“他人呢?”
“病了,在庄子里躺着。”
“什么病?”
“风寒——”
詹屏秀美的眉尖拧了起来:“那怎么一直待在庄上呢?把他接回来,我给他看看——”
聂安熬了一夜,身上的寒气近乎逼人,他垂眸凝视着詹屏,直看得对方忍不住朝后面小心的缩了一步。聂安逼近,几乎将对方抵在墙上,微微低头,在对方耳边轻轻吹了一下。
“詹屏大夫,不行。”
詹屏直视着他:“我不收钱。”
聂安忍不住笑了一下,一把将詹屏扯进院子,勾着他肩膀笑道:“是是,多谢大夫,先看看床上那个病人吧,至于公子,他好得差不多了,今天他当值,晚上就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