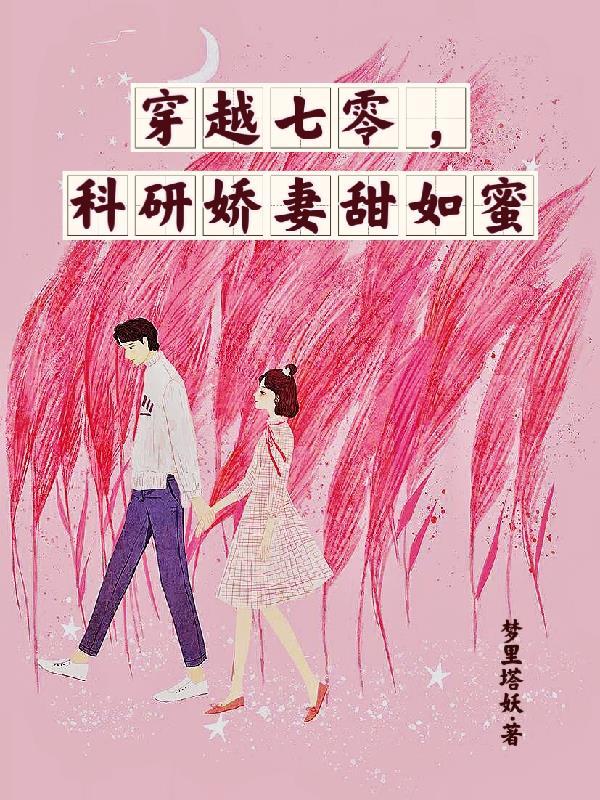车臣小说>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什么官 > 第79章 甘做小丑(第2页)
第79章 甘做小丑(第2页)
身后的陈远山见状顿时叫道:“他能进,本官为何不可进,这是何意?”
两个衙役赶紧竖起水火棍,满面苦涩。
“大人您莫要再为难小的了,老大人说了,您进去半步,打断我们狗腿。”
“慢着。”陈远山一指赵勋背影:“那是本官堂弟,本官要陪着他进去,快快让开,快!”
俩衙役根本不吃这一套,还表弟,之前这狗日的大半夜跑过来,非说大学官府邸着火了,还说厉沧均的母亲被火烧死了,结果厉沧均跑出来后直接被陈远山给堵住了。
当时厉沧均还纳闷呢,他老娘都死十来年了,好端端的怎么又死了一次。
州学衙署不像是衙署,从布局看的话,像是一个私人宅邸,大院,与赵家大宅倒是有几分相似,没有影壁,进去之后就是正堂,两侧各有三间班房,后衙也是一个大院,后为库房,左、右同样是班房。
不止是赵勋,府城很多人都想不通,大学官对陈远山好的和对待亲儿子似的,结果陈远山丝毫不领情,还总有冲撞之举。
午后静谧,学衙静悄悄的,各处班房开着窗,学官们趴在案头呼呼大睡,闲散至极,倒也没人见到赵勋二人。
没人领路,赵勋只能往正堂走,也是巧了,厉沧均刚伸着懒腰从正堂中走了出来。
厉沧均见到赵勋,满面喜色,连忙快步上前。
“好贤弟,你可算来了。”
几日不见,直接称呼“好贤弟”了,给刚要施礼的赵勋都整不会了。
满面红光的厉沧均不由分说拉住了赵勋胳膊,三步并作两步将其拉进了正堂之中,不忘回头喊一句“奉茶”。
赵勋坐下后,厉沧均抚须大笑:“愚兄昨日还思念着你为何还不前来,莫不是知晓险阻萌生退意了,是愚兄的错,贤弟非常人也,素有大志,心怀天下,岂会临阵脱逃。”
赵勋干笑一声。
其实这一声“贤弟”也不算无福消受,毕竟厉沧均这条贼船几乎可以说是注定要沉的,他所谓的梦想也是既不可望也不可及,赵勋过来开办学堂,那都是拿命在赌。
衙中是有文吏的,听到了叫喊声端着茶点快步走了进来。
文吏见赵勋面生,非但带着下人进来,还坐在了厉沧均对面,主要是大学官没坐主位,难免多打量了几眼。
待文吏离开后,厉沧均脸上依旧满是激动之色。
“肃县一别愚兄甚是想念,你可知归途中老夫观那三字经,观那拼音,越是看,越是心潮澎湃,好,好啊。”
赵勋哑然失笑,呷了口茶。
“既贤弟来了,愚兄这心也安下了。”
都能给赵勋当爹的年纪,厉沧均一口一个愚兄,丝毫不别扭,赵勋也慢慢习惯了。
“好贤弟,离别那一日你可是卖了大关子,说这学院要办又不可轻易办,待你来了再告知愚兄,愚兄整日心痒难耐,现在你可算来了,也该告知详情了吧。”
赵勋放下茶杯,坐直身体。
一看赵勋这模样,厉沧均也收起了笑容。
“府城之中,所有读书人,所有文官,没有任何人希望出现一家可以让百姓读书的书院。”
赵勋看向门外,压低了几分声音:“所以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老大人…一个老哥哥你为我量身打造,不,为这个书院量身打造的契机。”
“契机?”
“书院,要办,快办,但不能说是招收平民之子,而是招收达官贵人之子。”
“这是为何,达官贵人之子岂会入这书院就读?”
“要的就是他们不来。”赵勋嘴角微微上扬:“他们为何不来,因我只是举人,只是商贾之后,开办书院教学定会引来耻笑,可我赵勋是个要脸的人,要颜面的人,要脸的我恼羞成怒了,好,这书院办起来,没有学子,很丢人,恼羞成怒感觉丢人的我和疯子一般大嚷大叫,叫嚷你们这群达官贵人之子不来读,那我就教授平民之子,所以说,我赵勋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上蹿下跳让他们笑话,让他们耻笑,直到有一天,他们笑着笑着突然现,越来越多的平民之子,读书了,认字了,甚至可以考取功名了,虽然,到了那时我赵勋早已沦为满城笑柄。”
话音落,赵勋再次拿起茶杯,神情平淡。
再看厉沧均,突然站起身,朝着赵勋深深施了一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