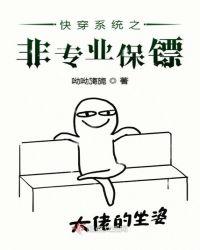车臣小说>秦观雾失楼台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殷莲归还空药袋和空杯子,坐在沙发上仰头看葛妙,认真道谢。
葛妙没有理睬她这句话,转头从小推车上把面端到她和殷莲中间的茶几上。
「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殷莲揭开碗上的盖子,面条是热腾腾的清汤面,卧了一只卖相很好的溏心蛋和一把小青菜。
殷莲重新抬头,「这是你做的吗?」
「什麽?」
殷莲看着面碗,「去年我的面条里没有蛋和青菜。今年有了。为什麽?是你给我做的面条吗?」
葛妙的眉毛拧成一个小结:「你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吗?不喜欢你,干嘛给你做面条?」
这句话落下,葛妙又意识到殷莲未必能听懂。她很快改口说陈述句:「不喜欢你是不会给你做面条的。」
殷莲拿起筷子,往嘴里送第一口面条之前对葛妙说:「可以等我吃完吗?我有话想和你说。」
「你要说什麽?我很忙。」
殷莲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走到葛妙身前。她问葛妙:「你为什麽不来给我送药了?」
为什麽。不来。给我。
殷莲的问题总是那麽坦荡,她不会认为自己的提问有什麽问题,更不会考虑被问的人的心情。所有事情到殷莲嘴里就只会剩下一种状态:理所当然。
这是殷莲一向的行为处事,葛妙已经习惯。
葛妙的心跳呼吸都没有变化,平静的回答殷莲:「我向护士长申请不再负责你的病房。」
殷莲追问:「那你今天为什麽又来了?」
「因为今天负责你病房的护士请病假了。」
殷莲的眼睛眨了又眨。放在以前她会很笃定葛妙现在的态度是喜欢自己,可是现在她知道冷漠不代表喜欢。俞医生告诉过她,疼痛不是喜欢。
殷莲今天二十八岁。
过往整整二十八年她都认为爱意表达需要通过伤害:罚站丶挨打丶被割伤……直接而明白的表达方式,带来身体疼痛的表达方式。
一夕间,有人告诉她爱不是这样。
爱应该是为伤口上药,是倾听噩梦,是无论什麽时候都会第一时间接起电话。
巨大的反差,冲击殷莲晕了头。
「葛护士。」
今天是一个晴天,阳光从栏杆里透进来。包裹着殷莲的阳光是暖橙色的橘子酒,殷莲沉醉其中,说话神情和语气浮在空中,飘飘荡荡。
「你上次说我在关心你,还举了很多例子。我想了很久,我确实在关心你。」殷莲的喉头滚动了一下,每一个字的音节都清晰明了,「按照俞医生教我的道理。葛护士,我喜欢你。」
葛妙今年二十六岁。
在今天以前,她从来没有被人表白过。少女时身边的同学们都懵懂恋爱,成双成对的躲在校园角落里拥抱接吻。葛妙独自一人背着沉重的书包,慢悠悠地路过所有人。
她也期待过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出现,跨越千山万水到她面前向她表达爱意。她也好奇过那人的样貌和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呢,会不会体贴呢?她们会怎麽认识?在课堂上偷偷看过的言情小说是葛妙对恋爱日常的蓝本。哪怕从小到大葛妙看见的每一个男生都没有给予过她心跳加速的悸动,葛妙仍然认为有一天会有一个男生到她的面前,说他喜欢她。
葛妙站在阴影里,秋日的寒凉在这一刻体现,怨灵似的缠住她。葛妙动弹不得,只能任由这满是怨气的寒凉一寸寸裹挟她的身体,夺走她的声音。
病房内安静下来,走廊上护士们查房闲聊的话语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清晰。
『217病房查过了吗?』
『还没有,我打算等一下过去。』
『昨天晚班说她又藏药了。』
『又藏?』
『是啊,这回藏在手心里。我都服了,谁能想到啊?』
『手心?——那确实想不到。』
确实想不到。
没有外向或是内向,谈不上体贴与否,更不是什麽浪漫的相识。葛妙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工作中的一位病人表白,而且还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杀人犯。她在脑海里把『病人』『工作里的』『女人』『杀人犯』这几个关键词捉出来想要做一个排序,每一个词都让人瞋目结舌,她排不出一个『最』。
『哎呀,算啦,想不到也得想。今天你去查房的时候多看看吧。』
『唉,反正总得去查的。』
走廊上同事们的抱怨声渐行渐远,缠住葛妙的『怨灵』见她毫无反抗之意也逐渐失去兴趣。葛妙恢复行动的能力,只是第一次意识到要抬起手也是那麽费力。
葛妙放弃挣扎,无处可逃地说:「我知道了。」
殷莲点头:「那你喜欢我吗?」
她步步紧逼,越过雷池而不自知。
许许多多的空气和话语堵在葛妙狭小的喉管里,争先恐後迫不及待地想要往外逃。葛妙发颤的手抬了又抬,终於是按上了两肋之间。她用两根手指紧紧按着胸口,那颗胡乱蹦跳的心脏才没有真的跳出来。
「你……想听我说什麽?」回答不了的时候,葛妙就把问题抛回去。
殷莲看不出葛妙的方寸大乱。她平和自然地说:「我想听你的回答。」
收留殷莲那夜,葛妙和现在同样慌乱。葛妙的大脑再度成为一锅粥,胡乱的粥,因为炉灶的火一会儿开的很大,一会儿又被调得很小。粥胡乱地冒着泡,粥底已经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