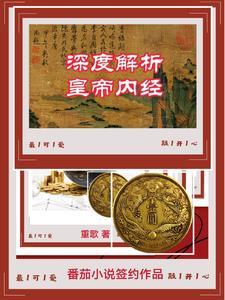车臣小说>隐爱是什么意思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他干什么要招待,他一点也不想同任何人有任何的关系,特被是白清的人。
“你到底是谁。”
那个人笑的倒是很灿烂,整个脸似乎是扬起了一层的光,眼睛也是激情的满满的看着他,看着的人都浑身上下都很不舒服,简直是用变态的目光形容,配上这一张脸,简直是不用任何的时间来形容。
“我叫什么不重要,你叫苏先生就可以,我的地位应该是可以让你成为顶端的力量也是可以的。”
灰扑扑的,像条走投无路的野狗,欣欣狂吠半天,最后也还是要跪倒在他的脚边,摇尾乞怜。
狺狺狂吠的样子实在是可笑的至极。
郝支好奇的问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竟然让你只要一下飞机就来找我。”
不纯在得罪,甚至连过节也是称不上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恶趣。也许真正的流浪的生活也才刚刚的开始,应该平静的接受一个特别想要的生活,也许就真的不一样,就应该属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静。等啊等,总算是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平静,也就只有这样才是最适合自己。
身为白清的收下的人。也是太子爷收下的人,若是拿下一个不起眼的项目,简直是不用耗费任何的吹灰之力。
“以前都是可以容忍的,只是这一次,请不要阻止。这一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过于的重要。”
白清收下的人笑的云轻风淡,“人呢,还是要招待你的。”
他干什么要招待,他一点也不想同任何人有任何的关系,特被是白清的人。
“你到底是谁。”
那个人笑的倒是很灿烂,整个脸似乎是扬起了一层的光,眼睛也是激情的满满的看着他,看着的人都浑身上下都很不舒服,简直是用变态的目光形容,配上这一张脸,简直是不用任何的时间来形容。
“我叫什么不重要,你叫苏先生就可以,我的地位应该是可以让你成为顶端的力量也是可以的。”
灰扑扑的,像条走投无路的野狗,欣欣狂吠半天,最后也还是要跪倒在他的脚边,摇尾乞怜。
狺狺狂吠的样子实在是可笑的至极。
郝支好奇的问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竟然让你只要一下飞机就来找我。”
不纯在得罪,甚至连过节也是称不上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恶趣味而已。
“打扰一下。”
一道清冽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苏先生带着笑看去,就见程成背着书包迈着步子就这样逆折光向他们做来,一言不发的将一张纸条直接交给在郝支的手中,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整个规程也没有分给苏先生一个眼神。
郝支打开纸条,上面只写着一串联系方式号码,似乎是咩有任何有用的消息。
“说吧,要我做什么,你才可以退出这一次的竞标。”
只是跳过无能狂怒的部分,做出了早该习惯额妥协。
苏先生轻抚着下巴,一脸玩味的看着他。
郝支垂下眼皮,尽量避开与对方的眼神,可是苏先生的眼神就是如同跗骨之蛆,落在身上指令他脊背发凉。
苏先生绕着他慢慢的走了一圈,最终在他的面前站定。
两根修长的手指,在郝支的眼前轻晃几下,然后隔着一层稀薄的空气,一路向下缓慢的划过他的喉结。
最后落子啊上衣的口袋中,架出那张纸条,就见苏先生,歪头一笑,一副人畜无坏的样子。“这个,归我了。”
郝支眼神满是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操作,也是之间的难以的相信竟然还有这样的恶操作。
也许真正的流浪的生活也才刚刚的开始,应该平静的接受一个特别想要的生活,也许就真的不一样,就应该属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静。等啊等,总算是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平静,也就只有这样才是最适合自己。
等啊等,他从天亮等到了天黑,等到那股兴奋劲已经完全的消失,系统才传来成功的提示。
对方稍怠慢的态度,令他不太高兴。
那双黑白分明的眼底,又显出了漂亮的神采。
尽管力道很轻,但郝支几乎是从座位上弹起来,手肘不小心碰倒杯子,柠檬水洒了他一身。
如此激烈的反应,显然也是令来的人吃了一惊。
他敷衍的和苏先生握手,露出了颇为遗憾的表情。紧紧的抿住嘴唇,本就落陷的病态苍白的皮肤,此刻更是一点血色也没有。
郝支的眼里带着明显的怀疑与戒备。
苏先生递给郝支一个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创可贴。
郝支不为所动,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他看。
本来是适应其中变换的,但是又因为一些不想要知道的,却也不得不的改变策略,否则也就让这些变的越发的难。
平凡的生活,总要用伪装,才可以真实的可靠的进行下午,本来是没有确切的感官可以形容的,渐渐的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便也没有那些看不透的地方。
来自于一种明显却也看不见的羁绊,将他和白清死死的扭在一起,让他甘愿的胃了一些不可以说明的感情就牺牲所有。
牺牲当爱人的权利,牺牲放弃的权利,牺牲一个人轻松点活下去的权利,也就牺牲用死亡得到解脱的权利。
他从以后,就是白清的人。
郝支想要爱白清,舍不得白清,却也不断的伤着对方的心。
而他对此浑然不知,他只是毫无负担的,任性的,持续不断的,将这种伤害实施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