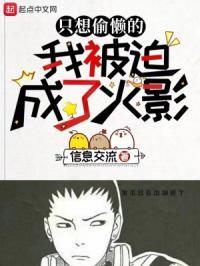车臣小说>救赎了我是什么意思 > 第25頁(第1页)
第25頁(第1页)
那時候他的手算不上很巧,努力了半天依舊是亂糟糟的雞窩頭,春歸還被他嘴裡銜著的香菸燙了一腦袋灰,鬧得晚飯也不肯吃。
後來沈雪遲專門買了一個假人頭放在辦公室,偷偷練習。
不過等他終於練好了,春歸已經喜歡上了年輕人之間很流行的狼尾頭,要長不長的,扎不起來,但吃飯時頭髮總會掉下來幾綹,沈雪遲便去買了幾隻水晶髮夾,一到吃飯的點就習以為常地給青年卡上。
春歸突然想起二中的校規不讓男生留長髮,他不想聽李詠嘮叨,也不想去理髮店,他用腳尖踢了踢男人的小腿,在對方轉過身時,兩隻手斜捧在臉下,裝自己是一朵小花:「給我剪頭髮吧,剪丑了也沒關係,我不會怪你。」
沈雪遲嘴上說著倒不如剃個光頭,身子卻老實地走到桌前,拿出抽屜里的剪刀,他可能早就想這麼做了,連打薄款都有。
浴室堪堪容下兩人,經年不見陽光,牆壁有些發黃,但看得出住著的人存在潔癖,角落沒有霉點的跡象,防水簾也是的。
沈雪遲拿來一個小板凳讓春歸坐下,簡單地用一塊毛巾圍住春歸的脖子。
春歸笑道:「人家是擋碎發的,你倒好,這下全掉我身上。」
男人也不惱,但把頭髮全部梳他眼前,讓他什麼都看不到。
「沈雪遲。」春歸閉著眼,聽著剪刀在自己耳邊咔擦咔擦的聲音,他把纏繞自己心中好久的問題終於吐露出來:
「那你呢?為什麼要同意和我做朋友,甚至未來都要把我安排進去?」
沈雪遲只顧著手上動作,一時半會沒有說話。
怨嗎?其實他的心中是怨的吧。
他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他沒有解開手銬,結局會不會稍不一樣,可春歸的心怎麼會這麼狠,就連生日都不肯過完。從窗外順著管子爬上六樓,到一定的高度跳下,沈雪遲在與他手指擦過、跟著跳下去的瞬間竟奇蹟般地想了許多。
他想會不會是自己對春歸太過溺愛,一直維護著對方心中理想的烏托邦。
眾生平等,即便身份地位懸殊,貧窮或富有,他們依舊是人。
笑話。
若是二十出頭年輕氣盛的年紀,他大抵真的會打斷春歸的腿,把人整日鎖在床上。
可就連最後,他都選擇了最溫和的處理方式。
原來他才是那條被牽著繩子的狗。
沈雪遲說:「——」
春歸的頭被男人用手固定住,動彈不了,剪刀聲還未停止,碎發落在少年的眼皮上,毛茸茸的,癢得慌,他忍不住拱拱鼻子,聽見頭頂上方的人在說話,他立直脊背,想更靠近對方一些。
春歸問:「你說什麼?我沒有聽清。」
剪刀聲停止了。
沈雪遲用手拂去春歸臉上的絨發,以上位者的姿勢凝著他,可開口時男人卻俯下身,與他平視,眼神渴求到好像要把他塞進眼裡,男人輕聲道:「所有你不知道的事,你想聽的話,我以後慢慢和你講。」
-
春歸今晚要在這裡睡下。
其實沈雪遲是不願的,這裡過於簡陋,空氣也潮濕,仔細聞的話還有一股霉味,不好的東西他無論如何也不想獻給春歸。
春歸置氣問:「那你要我來你家幹什麼?給我剪頭髮?」
沈雪遲被他狠狠哽住,不再說反駁的話。
他從衣櫃裡拿出一套加絨睡衣遞給春歸,這裡沒有空調,但冬暖夏涼,倒也能湊合。
不過他的睡衣對春歸來說還是大了,少年看著拖到地上的睡褲,和把自己手掌全部遮住的長袖,不由得懷疑他們初次見面時的身高相當難道只是自己的錯覺。
春歸洗澡沒有擦頭的習慣,但沈雪遲就像料及到一般,拿著乾淨的毛巾早早坐在床邊等候。
沈雪遲說:「把頭髮擦一擦。」
而春歸的回答也在他的預料之中,可男人偏要多此一舉問他一嘴,好像這樣就有了接近他的正當理由。是他讓我這麼幹的,如果我不擦,他肯定會感冒,沈雪遲這樣想到。
浴室里嘩啦啦的水聲再次響起,春歸站在屋中央,突然想起自己還沒有看沈雪遲給他剪的頭髮,索性踩著大自己好幾碼的棉拖鞋趿拉到桌前。
筆記本電腦處於休眠狀態,估計是從哪裡淘來的二手,春歸越過它拿起鏡子,左右看了看,發現自己的鬢角和額前都短了些,看著精神許多,現在他可以承認男人的技術確實不錯了,至少沒有讓他非常難看。
正準備將鏡子放回原處,他頓了頓,拿起下面墊著的那張照片。
上面的人他不認識,指不定是沈雪遲父母的舊照,他下意識翻過背面。
「……oo528?」他疑惑道。
-
水聲停止,沈雪遲粗-喘了一口氣,雙臂撐在兩側,他抹去鏡面上的水霧,沉默地與裡面的人對視。
他說:「你確定要把現實代碼告訴他?即便這會導致他『再次』毀滅?這是一個愚蠢的選擇,你已經犯過一次錯誤,難道你還要——」
他說:「我很怕,可我……」
他說:「我想看看,或許他能……」
「未來」,他敏銳地捕捉到這個詞彙存在的問題。
春歸考慮的始終是有他的未來,卻從不顧及自己的未來。
結合種種,他在那一秒幾乎能想到很多關於春歸行為的解釋,卻從沒直視過那唯一一個占據心臟中央,溢滿都要浮於表面的選項——春歸在救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