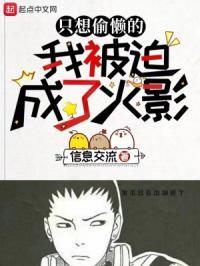车臣小说>爱谁谁爱谁谁下一句幽默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夏锦时只好自己独占了一个院子,十分不好意思。
转眼上元节已至,夏锦时早就在京都的一家酒楼抢定个了桌位,三人准备饕餮一番,然后去赏上元夜的花灯美景。
等着上菜时,钱浅注意到钱绵绵盯着门外卖冰糖葫芦的,于是出去给她买。买完糖葫芦,又注意到一旁卖花灯的摊子上,有一盏画着一男一女看着弯月的灯笼,突然被拨动了心弦。
小贩见她一身富家女的打扮,满脸堆笑相迎:“姑娘,您瞧这画画的多精致啊!这灯今日拿着,特吉利!预示着您这一年都圆圆满满、和和美美的!来一盏?”
钱浅有些出神地应道:“好。”
“好嘞!六十铜钱。”小贩取下灯,等着钱浅付钱。
钱浅从钱袋子里数出六十铜币递给小贩,身后突然传过马蹄声,然后热闹的人群忽然嘈杂、激动起来。
她回身望去,千盏花灯地辉映之下,宋十安骑着高头大马而来,锃亮的铠甲,好似将整条街上花灯的萤火都吸到了他身上,那样的威风凛凛,又意气风发。
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
钱浅呼吸凝住,隔着人群遥遥将眼神锁定在他的身上,将他整个人望入眼底。
周围的嘈杂声与人群的躁动仿佛全部消失了,先是一阵耳鸣,然后便是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声音震耳欲聋。无数次在脑海中描绘过那光风霁月的模样,与眼前这身形挺拔严肃之人逐渐重迭,少了一丝温润儒雅,多了些不怒而威的气势。
“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原来描述的就是这般景象。
好久不见,宋十安。
钱浅在心里与他打了个招呼。
宋十安坐在马上居高临下地问下属:“可有异样?”
如今并无战事,他受命协同禁卫军维护治安与城防事宜。今日上元节,人多纷乱,他四处巡查,确保节日顺利结束。
下属行礼禀报:“禀将军,一切安好。”
“嗯,天干物燥,定要打起十二分小心。”宋十安交代着,突然感觉到一丝异样。他抬起头,向那个方向看去,那里很多人看他,但那个感觉却又没了。
钱浅见宋十安望过来,连忙低下头,转身就跑了。
小贩在后叫呼喊道:“哎姑娘!你的花灯!姑娘!”
宋十安已经下马来到摊子前,四下张望,可那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
花灯小贩边将灯笼挂回去边嘟囔:“这算怎么个事儿……”
宋十安一眼瞥见小贩手中那个外形普通的灯笼,画上一男一女看着天上的弯月,抬手摸上去,问:“今日是上元夜,画上为何是弯月?”
小贩笑呵呵地说:“官爷,画圆了就不好区分是日还是月了呀!这少了一大半,画成弯弯的,就只能是月了嘛!”
“这个灯笼怎么卖?”宋十安取下灯笼握在手中。
小贩迟疑地说:“这个六十铜,但是刚才有个姑娘付过钱了,只是灯笼没拿走。”
“等那位姑娘再来,请她随意重选个吧!”宋十安掏出一枚银币塞给小贩,提着灯笼走了。
小贩困惑地挠挠头,自言自语道:“这灯笼好几日都没人问过了,怎么这一会儿就有俩看上的?”
钱浅三人饱餐过后走到街上看灯。
花灯摊贩眼睛极尖,一眼便认出了钱浅,叫道:“哎!姑娘!”
钱浅此时已经回过神来,并不想要那个灯了。
小贩却向她鞠躬道歉:“实在对不住,刚才您看上的花灯,被一位公子买走了。那公子付了一银币,说姑娘可以随意重选个。”
夏锦时凑过来:“还有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钱浅也很高兴,问道:“那一银币是不是够买三个灯笼了?”
小贩赔笑说:“那个灯笼属于您,一银币都是您的。但花灯价格不同,您看看想要哪个?”
最终又加了十铜,姐妹三人一人选了一个精致漂亮的花灯,开开心心提着去逛灯会了。
次日,钱浅开始到云王府“打卡上班”,谨小慎微地茍着。
给云王写传的日子,出乎意料的轻松。
王宥川并不似传言那般脾气暴戾、强横霸道不讲理。严格意义上说,他与钱浅前世认识的许多资质平平,却自视甚高的富二代们没什么两样。
她有点懂他们的心理,有人一生拼尽全力到不了罗马,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无数人羡慕他们的身份地位、权势财富,却不知正因为他们什么都有,才会陷入到无法得到成就感的苦恼里。
就像王宥川,他爹是皇帝,他母家祖父是大瀚第二首富,这辈子除非他也成为皇帝,否则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超越长辈的成就,那他永远都会被人当做活在“荫庇”下的纨绔子弟。
可他偏偏是个资质平庸的人,文不成、武不就,虽然眼高于顶,实际心里却虚得很,生怕被人瞧不起。
所以他虽脾气大,但本性还是良善的,不是肆意欺凌弱小的那种人。
钱浅谨记夏锦时的叮嘱,说话总会斟酌再三,又事事谨慎,总是躲在人后角落,拼命降低存在感。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倒也融洽祥和,从没惹到过那位小霸王。
她主要是记录下王宥川的喜好、擅长之类,并不用日日都去王府。王宥川只会在想让她来,或者有活动安排时,才会吩咐人来家里通知她。
钱浅时间比较充裕,所以仍会写话本卖钱增加收入,准备给绵绵买下间铺子,把锦绵阁挪到地段更好的街上。
细碎的时间,她就会去打理家中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