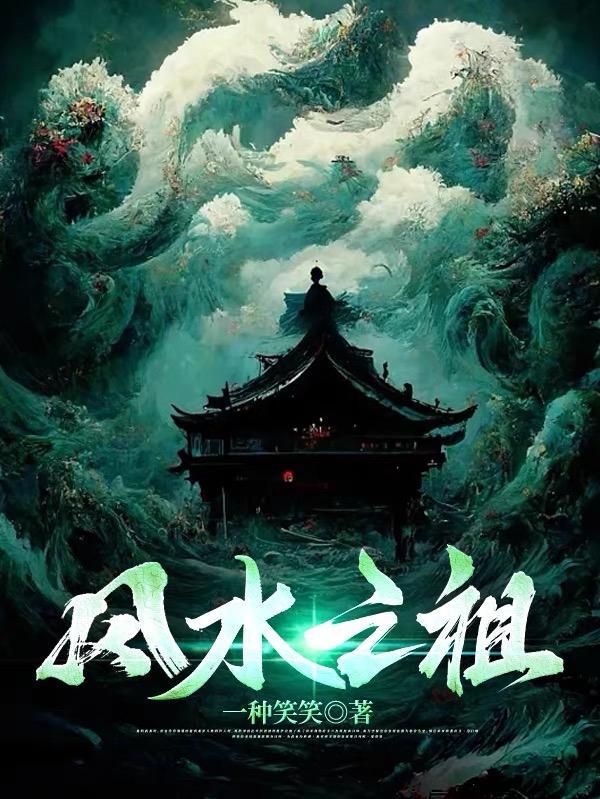车臣小说>王妃不侍寝作者唯我天下 > 第八十一章 美人有疾(第2页)
第八十一章 美人有疾(第2页)
婢,居然敢拦我!?”
贱婢?我是贱婢?我默了默,看来还是缺乏了一丝王妃的气质,以后该端起架子的时候就该端起架子了。
“你又是哪里来的疯丫头?”我抬着头,心情不好自然无好脸色,语气更加是无以复加的差,“快点滚出去,不然我喊人了。”
十五年来我似乎都没对谁说过这么严重的话,如今看来,我也是能说的,且说起来毫不逊色,原来我也有这么狠戾的一面,或许在外人看来并不狠绝,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似乎是真的变了。
那少女的确是愣了愣,张着嘴一时不再大声喊叫,忽然转了转眼珠俯身露出一些哀求的神色来:“好姐姐,你就让我进去吧,姑娘在里头危在旦夕,我手里有些琉璃散还能缓缓。”
琉璃散?那又是什么?
我问她:“你们家姑娘得的是什么病?”
少女眼神有些飘忽,神色中的哀求转瞬即逝:“这是秦姑娘的私事,外人还是不要干预为好,让我进去或许还能吊着姑娘一口气。”
我皱了皱眉头,虽然觉得很是不妥,但一听却有些道理可循,于是便退让一步:“好,你进去吧,记住不要大声喧哗。”
我自知板着脸脸色铁青,但心里还是不好受,喜怒形于色,这话说得在理。
那少女一见我松了防线便撞开了门闯了进去,一边从怀里摸出一只药瓶子,跑到床前跪在地上,颤抖着手导出一些药粉喂进
顾青怀的嘴里,从桌上倒了一杯水喂了进去,难道这些白色的粉末就是所谓的琉璃散?
只见水流沿着顾青怀的嘴唇缓缓流进了一些,顾青岚便呛醒了,一醒来便猛烈地咳嗽,舞着手臂扯着那名少女的衣襟不放,手指攀着那只盛着琉璃散的瓶子,伸出舌头去舔那些洒在外头的药粉。
我立在门口已是惊呆,这样的顾青怀真是从未见过,像是被一阵无形的力量操纵着,不由自主地去舔舐那些白色的粉末,这琉璃散到底是何物?怎的如此厉害?
琉璃散……似乎听我爹提起过,那时我爹从西域经商归来,就带过一种叫做琉璃散的药,这种药看似为药,实则为西域奇毒,一旦染上,便会成瘾,看来风越楼是将这种毒用作控制歌女与琴女的工具了。
顾青怀吃了那些粉末后便安分许多,瘫软在软垫上,一言不发,双眼空洞无神毫无焦距,我看了有些心悸,原来她也是不幸之人,这琉璃散总归不是好东西,不能再吃了,不然迟早得折在这上头。
那端沐臻定是与我生出一样的疑惑,早已夺来那只瓶子细细的探看,以他的见多识广一定也听说过这种大名鼎鼎的西域奇毒,果然他只嗅了嗅便将瓶子放在一旁,厉声问那名少女:“你是何人?”
少女满脸担忧,又带着点不满:“奴婢宣儿,是秦姑娘的贴身侍婢,姑娘若没有琉璃散,定活不过今晚,
还是让宣儿来照顾姑娘吧。”
“谁允许你们给她用琉璃散的?”沐臻明显脸色不快,执着那只药瓶厉声责问那个名叫宣儿的少女。
“王爷犯不着来管风越楼的事,姑娘虽被王爷赎了身,但却离不开琉璃散,不日还是会回到风越楼中去的。”宣儿直视着沐臻,毫无惧色,敢冲撞高高在上的王爷,她的胆子应当也不小。
我暗暗替宣儿捏了一把汗,若方才她没说今晚会照顾顾青怀,沐臻怕是早就不将她放在眼里,唤来那些暗卫将她除去了吧。
唉,这风越楼里的小小婢女怎都如此大胆,那这背后真正的东家又会是怎样的人呢?
我不敢去想象,光就风越楼控制歌女舞女的手段来看,就很是高明,这些女子想必一定过得很是凄惨悲哀,被人当成木偶一般操纵,站在台前受到万千宾客仰慕追随,可幕后却活得生不如死。
琉璃散究竟该如何解呢?
而顾青怀为何没有死,而是出现在了宁州城里的风越楼?
房内沐臻依旧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此时的表情,他一定又无奈又愤怒,这琉璃散的毒怕是早已彻入顾青怀的骨髓,而他却是束手无策,只能任凭宣儿给她喂下一瓶又一瓶的琉璃散。
我悄悄挤进了门缝,屋内比外头暖和不少,拧拧头发上的水,缩着身子躲在一座插屏后往那温暖处靠了几分,就听那边顾青怀苏醒过来一些,喃喃着不知在说些
什么,沐臻坐在她身旁替她顺着气,一手执着一只杯子就要给她喂水。
没想到他也是个能照顾人的,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曾这么照顾我,顾青岚娇弱的身躯无力地瘫在软枕上,楚楚可怜的眼神就像是一只受惊了的小白兔,亟待关怀与垂怜,两道秀眉微微蹙起,平添一分怜惜之感,即使病了仍是风姿绰约,如斯美人谁人不喜,谁人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