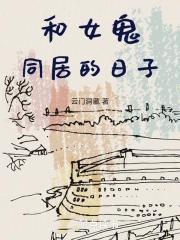车臣小说>太子妃失踪了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看门的老宫监禀告说虞府来人了,三人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
虞向晴沉默半晌后吩咐道:“她们有何事就在院子外边说了便是,不必迎进来。”
她话音未落,虞府的徐嬷嬷就带着人乌央乌央的进来了,十分不见外。
徐嬷嬷满脸堆笑在虞向晴跟前问东问西的,一副十分关心惦念虞向晴的模样。
她边说边跟身侧的小丫头使眼色,那些小丫头们齐齐将碧桃碧月围住,然后经验老道的婆子鬼鬼祟祟的往虞向晴的卧室里钻。
虞向晴眉脚一跳,怒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让开。”
徐嬷嬷面色一僵,仍涎皮赖脸的往虞向晴面前献媚,碧桃身子高挑,三下五除二剥开了围绕着自己的小丫鬟,她不经意一抬头,正看到虞府的一个婆子往虞向晴的卧室里钻,不禁怒道:“也是大户人家调教出来的奴才,怎这般不守规矩,太子妃的寝殿是你们这群腌臜货说进就进的吗?”
虞向晴闻言脸色一变,忙推开徐嬷嬷往卧室里走,此时那个塞纸人的婆子正在虞向晴床帷处摸索,见她床头摆放着一本梵经甚觉新奇,以为是什么名家抄本,心想着暗悄悄的塞进怀里带出去卖掉换几两赌资,不料却被闯进来的虞向晴逮了个正着。
虞向晴不由分说向前抢经书,几番拉扯下,刺啦一声,经书被扯破,那婆子尴尬的松了手,臊眉耷眼道:“奴婢看经书上落了些灰尘,想伸手拿袖子掸掸,没成想好心办了坏事。”
“啪”的一声脆响,此婆子被人抽的像陀螺一样转了好几圈,碧桃撸袖子怒骂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碰娘娘的经书。”
两方劝的劝,骂的骂,乱作一团。
虞向晴捧起散落一地的经书,钻进高脚桌底下默默流泪,双手颤抖着去拼碎掉的经书,却发现怎么拼都拼不起来,神情越发的焦躁。
碧月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她守在高脚桌子旁,被乱哄哄的人群推搡的歪东倒西,虽是如此仍拼命护着高脚桌的安稳。
恰在这时,辛颂骑马停在溶月山庄门口,却见守门的奴才都不见一个,不禁皱了皱眉头,他翻身下马往里走,内室的哄乱声大喇喇的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去,他神色一冷,阔步进门。
跟在辛颂身旁的太监清了清嗓子,高声唱道:“祈王殿下驾到。”
屋子里的人瞬间一怔,忙骇的倒地便跪,行大礼道:“奴婢见过祈王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辛颂眉头紧拧,问道:“何事如此喧哗?”
碧桃见辛颂来了,顿时松了一口气,她一五一十的将徐嬷嬷等人的行径说来,越说辛颂的脸色愈沉。
末了,辛颂道:“往日本王听说豪家骄仆,恣肆放诞,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徐嬷嬷吓得瑟瑟发抖,偏偏那闯了祸的婆子不知死活道:“殿下,奴婢冤枉啊!”
辛颂并不听她辩解,只对身后的高远高扬说道:“押送去长安县衙,命县令好好研判此事,县令判不好便提到刑部去。”
“属下遵命。”高远高扬领命后,便压着一众丫鬟婆子去了衙门。
虞向晴仍躲在高脚桌下拼梵经,好似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一样,边拼边喃喃道:“拼不好了,拼不好了。”
辛颂心头遽然一痛,他亲自轻轻移开高脚桌,亦俯身蹲在虞向晴身侧,伸手握住她的手与佛经碎片道:“没关系的,拼的好,让我来试试?”
虞向晴猛然一扭头看到了辛颂,突然扑进他的怀里放声大哭道:“都是我不好,弄坏了经书。”
豆大的眼泪顺着辛颂的颈侧直往里钻,烫的他心都碎了,不知为何他就是见不得她哭,仿佛他曾见她哭过千千次,再多一次他便承受不起。
半晌后,辛颂深深吸了一口气,将佛经的碎片集齐,一边阅读一边比对,他命下人拿来浆糊,小心翼翼的拼凑着,虞向晴抽抽搭搭的坐在他身侧,十分乖巧,望着他深邃的眉眼问道:“真的能拼好吗?”
辛颂回眸一笑,极美的桃花眸子温柔又多情,他坚定的回道:“能的,相信我。”
二人拼了半个时辰才将经书拼凑完整,虞向晴像得了无价之宝似的紧紧搂在怀里不放,走到哪都得带着。
辛颂莞尔一笑,命人去闻月山庄取了一只十分精美的螺钿匣子,不到一尺长,正好可以放下经书,还带有一方连环锁,他将盒子交给她,亦把钥匙交给她,教她将佛经放在盒子里,把盒子放到床边柜上,她只须拿着钥匙即可,里面的宝物谁也夺不走的。
虞向晴爱惜的摸摸胸前的钥匙,问道:“这样真的可以了吗?”
辛颂点头肯定道:“自然。”
虞向晴终于破涕为笑,开心了起来,忽而她问道:“不行,今天的功课我还没做。”
辛颂道:“今日歇一天,我重新抄一本一模一样的经书给你。”那本到底出自她的情郎之手,又破损过,虽然粘好了,到底不便翻阅,等她清醒了不定如何心疼悔恨呢,不如重新给她抄一本。
辛颂抄经抄到半夜,虞向晴守在蜡烛旁打瞌睡,怎么都不肯去睡觉,直到辛颂将经书抄好,离了溶月山庄,她这才心满意足的去休息。
然而,辛颂并没有回隔壁的闻月山庄,而是打马入城进了宫。
熬夜批奏章批到大半夜刚刚躺下的太子,被辛颂从被窝里提了起来。
“雉奴,怎么了?”太子揉着惺忪的睡眼困倦的问道。
“阿兄,你是太子,得主持公道。”辛颂直言不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