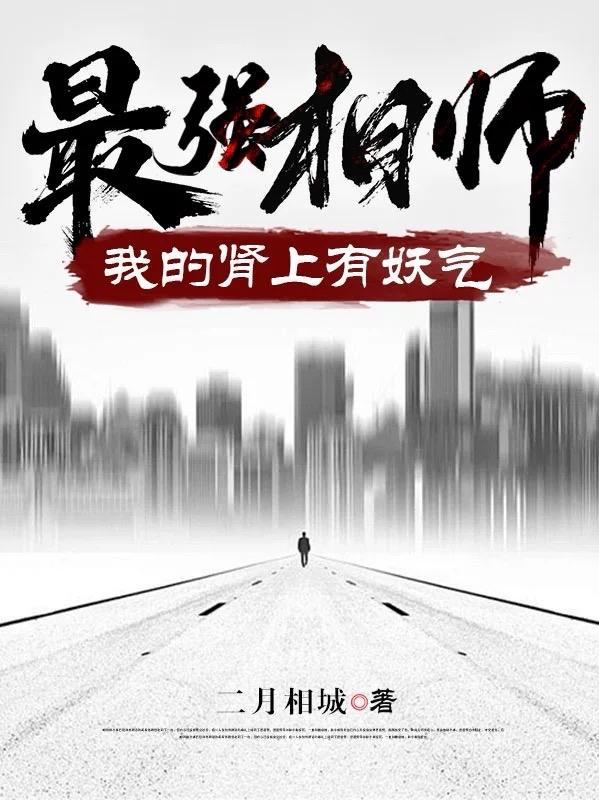车臣小说>总裁他脑子有病 笔趣阁 > 第128章(第1页)
第128章(第1页)
言罢,推开椅子大步离去。
做到睡着为止
段氏大楼。
已经过了下班的点儿,楼里除了些加班的员工,没多少人。
副总裁办公室仍然亮着,段承泽开了一天的会议,刚回到书桌前处理积压的文件。
纪繁清给他捅了不小的篓子,但也算不上致命,集团树大根深不会那么轻易就撼动根本,只是处理起来有些麻烦。
公司的声誉一旦受损,消费者的信任很难再次建立,竞争对手也趁着股价动荡期间,浑水摸鱼恶意收购。
如今段父基本已经退居幕后了,台前的工作全权交给段承泽在处理,这段时间他每天重复着各种应酬、开会、加班,胃病反反复复,是以整个人看起来迅速消瘦了下去,两颊都明显较之前凹下去不少。
如果细看的话,额角还多了一道浅浅的疤。
段承泽揉了揉眉心,刚批完一份文件,门外传来秘书的喧哗声。
“不好意思,纪先生,您不能进去!请您稍等,容我先通传一下!纪先生——”
砰的一声,大门被直接推开。
纪繁清脚步不停,在段承泽错愕的目光中,走到桌前抓起一迭文件,扬手砸在了他脸上。
秘书尖叫一声,要跑过来。
段承泽偏着头低喝了一声:“出去!”
秘书咬唇顿足,白着脸退出去顺便带上了门。
室内安静下来,纸张飘落一地,段承泽从位子上抬眸与他对视:“……气还没出完?”
他面色沉静,语气纵容,仿佛在面对一个闹脾气的小孩,而他是那个成熟包容的大人。
也是,在香港时纪繁清就砸了他一红酒瓶,回来后又爆他公司的内幕,那些资料,他应该是早就着手在收集了,就等着这一天派上用场捅他一刀,但凡换个人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纪繁清能安好地站在这里,趾高气昂地再次给他甩脸子——
“你也就仗着我喜欢你而已。”
“喜欢我?”纪繁清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你懂什么是喜欢吗?段承泽,你只是喜欢看我孤立无援时只能依附你的样子,那样你很有成就感是吧?你看我是不是看一只蝼蚁一样,可以随便任你摆布?”
“我没有……”
“不重要了!”纪繁清打断他:“我现在只希望从来没有认识过你,如果当年我和叶回没有错换身份,最先和你相识的应该是他吧,要真是这样就好,你们倒是挺配的!”
“纪繁清!”段承泽沉下了脸。
“怎么?觉得膈应?恶心?”纪繁清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苍白的脸有一种诡异的妖冶,像是美丽的毒蛇在酝酿致命的攻击:“你知道吗,你说喜欢我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
段承泽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僵在原地,语言是一把无形的刀,伤人不见血,却刀刀致命。
段承泽只觉胸口剧痛,而纪繁清的眼里有着毫不掩饰的快意,每一道冰冷的视线,都像一道利箭穿胸而过。
“恶心得要命!”
段承泽双目死死地盯着他,喉间漫上滚烫的血腥气:“那谁的喜欢你觉得不恶心?靳逍?跟他上床你很爽是吗?”
电话里的喘息声忽近忽远,如鬼魅般在耳侧萦绕,面前的人逐渐幻化成另一副浪荡的面孔,在他人的身下婉转呻吟。
段承泽太阳穴突突地跳,心底的怒火忽然喷薄而出,抓起手边的东西就砸了出去:“纪繁清,你怎么那么下贱!”
烟灰缸落地滚了几圈才停,纪繁清侧身避开却还是被刮到了脸颊,颧骨上擦出一道红痕,但他面不改色地继续道:“我跟谁上床,下不下贱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第一,叶回的账我正在和他清算,如果你因为叶家的关系选择帮他,别怪我把段氏一起拖下水,大家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第二,如果你再敢对靳逍下药,做出之前类似的事,我一定加倍地奉还在你身上!至于是什么药,那就不好说了,但你一定不会比他好过!”
他眼底闪动的决绝,仿佛一个疯狂的亡命之徒。
段承泽被震慑在了原地,艰涩地开口问他:“你爱上他了……是吗?”
面对同样的处境,靳逍却做出了跟他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纪繁清放下了戒备,彻底爱上了他!
而这一切,是他促成的,是他成全了他们!段承泽忽然低哑地笑出了声,笑得面容扭曲,笑得眼前一片模糊。
“与你无关。”纪繁清冷漠地转身:“记住我说的话,请段总你好自为之!”
离开段氏大楼,夜幕已经降临,天空变成很深的蔚蓝色,纪繁清将车开到公园边,熄火下了车。
公园前面有一条河,跨上石桥,可以看到下面流动的河水,水面波光粼粼,折射着两侧沿岸璀璨的霓虹灯。
纪繁清站在围栏边,静静地吹着夜风冷却自己,风拂过脸颊,带来轻微的刺痛感,颧骨处已经肿起来一小块。
他低头看了眼水面,水波晃动看不清自己。
他的面目已经模糊了,他的过去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而前方的道路,只剩下一条。
他要叶回付出代价!他要他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手机铃声响起,纪繁清收回思绪,低头看了眼,屏幕上显示“靳逍”来电。
那一刻,纪繁清飘荡在半空的灵魂,仿佛暂时安稳地着陆。
他接起来喂了一声,靳逍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在哪儿呢?下班这么久还不回来,我饭都快做好了。”
纪繁清垂下眸,水面的波光映在他的眼底,如星光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