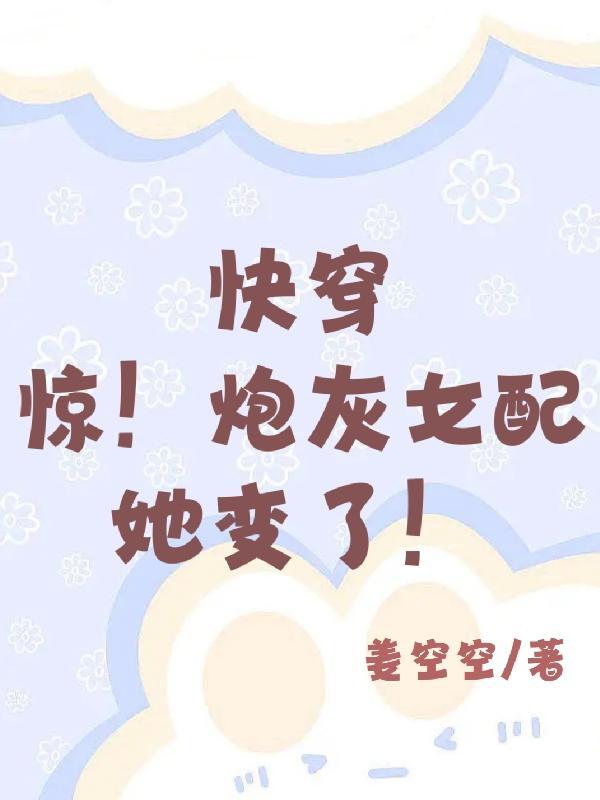车臣小说>猫是人间的龙[玄学 > 第49章(第1页)
第49章(第1页)
墨观至禁不住笑起来。
小黑猫来到人类的脚边,先是对准他的脚踝来了一记不轻不重的猫猫拳,仿佛在质问人类为何如此磨蹭让小猫咪在一旁空等。而后,小黑猫大度地放下小节。他的两只前爪踩上墨观至的鞋面,攀着他的裤腿蹭蹭登上粉色小三轮。
早已载不知多少的小三轮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
小黑猫别起耳朵,沉默片刻,装作无事生的模样,踩着墨观至的腿一路来到车把手位置。他将自己挤在车头和墨观至胸口之间,两只前爪揣起来,眯缝双眼瞪向胖橘等。
之前墨观至和燕鑫淼谈话时,其余四人一猫皆是听得津津有味。此时见到小黑猫,不知是不是错觉,墨观至总觉得那几只都规矩不少,或是别开视线,或是看东看西,一脸此事与我无关的风轻云淡的模样。
小黑猫张开口,嗷出一串不明所以的喵喵语,语气听起来不怎么友善。墨观至自然是没听懂,却见臧小欢等人一脸恍然大悟,争相点头。
白芝率先说道:“不如这样吧,既然老板还要面试观察我们几个,不如就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四人吧。如果我们表现得好,那老板就将我们都收下。我们先随这位先生去看看他的鱼塘,老板就留下来陪……呃,留下来玩耍吧。”
如此,还不等墨观至表意见,几人连同燕鑫淼都没有意见。燕鑫淼大约是对能传单的胖橘家族有着莫名的信心,不等白芝等人开口,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他们。一行人就这样有说有笑地走远了,顺带带走了完成接引任务的胖橘。
原地只剩下一人一猫,和一辆吱吱嘎嘎的小三轮。
墨观至眨眨眼睛,低头看去小黑猫,温柔地摘去毛脑袋上的红叶,问道:“那么接下来,你还安排了什么节目呢?”
小黑猫惬意地眯起眼睛,胡须骄傲地翘起,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色。
墨观至不由得对自己接下来的冒险生出些许好奇和期待。
一人一猫独处的画面其乐融融,那头贺老汉和严粟的谈话气氛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
严粟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贺老汉解释他们祖孙俩身上出现的症状。简而言之,那天进入芙蓉村的贺老汉和贺长生都并非是真人,而是他们的魂体,也就是通俗而言的离魂。
而贺老汉进入关口年纪,本身阳气弱,又因担心孙儿的情况,焦急之下也跟着离魂。幸而有巫元先前赠与的符箓镇魂,这才没有伤其魂魄。
有芙蓉村古怪的灵场加持,贺老汉看着和常人无异,唯有一见面就触碰到他胳膊的墨观至敏锐地察觉出些许异样。
在贺长生的记忆里,他是跟着爷爷的背影才来到芙蓉村的。然而实际上,原本是他因着血亲因果,且小孩魂体不稳,才不知不觉地被招到芙蓉村的灵场。
严粟说得委婉,贺老汉却一下子就听懂了。这便牵扯出一桩陈年旧事来,贺老汉不欲多说,满脸的褶皱抖得厉害。幸而严粟也没有要在细枝末节上刨根究底的意思,很快就笑着转移了话题。
他道:“老先生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事。鲤鱼阳气重,回家后让你家中晚辈买一条活鲤鱼烧给你吃,平日里多晒晒太阳,也就行了。”
毛春便有给进入关口年龄的老人购买鲜活鲤鱼的传统。在民间传言中,鲤鱼越过龙门即为龙,而龙是至阳之物,由此鲤鱼也被视作富有阳气的生灵,经常被当做求子的福兆。传统年画中,总是会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抱着一尾红艳艳的鲤鱼,寓意正来自于此。
贺老汉沉沉叹气,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一个劲点头。
如此一通交代后,为表诚意,严粟特地开车将贺老汉祖孙二人送回家。这一次,他身边只带着一位名为柳槃的女队员。目送祖孙二人进入家门后,汽车再次上路,严粟打转方向盘,毫不犹豫朝着一个方向驶去。
柳槃看出严粟的打算,犹豫道:“严队,我看毛春这里还挺看重冬至的,一定要今天赶着去审吗?万一撞见人家阖家团圆的,多尴尬啊。”
严粟重重吐出一口气,脸上又恢复了几分戏谑的神态。
他回道:“也不是我想加班加点呀,你仔细品毛春附近的炁场,越来越凶,已经不是小打小闹就能控制得了的。这事情拖不得,迟则生变。早一日寻到源头,就能给找到解决方案多留出一点时间。何况,经历过芙蓉村一案后,我看那两个女人家里恐怕不会太平,过不过节还是两说呢。”
柳槃闻言,也是暗自叹息,不再多言。
两人驱车来到姚立家,果然如严粟预料的那般,偌大的别墅中装修得富丽堂皇,却依旧显得空空荡荡,没有一丝烟火气。
而他们要找的人就坐在豪华的真皮沙内,一脸平静,好似早已预料两人的登门。
严粟也不客气,直接走过去,径直挑了一张看起来就很舒服的单人沙坐下来,正好直直对上姚立。
“姚女士,”严粟笑得灿烂,“我想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不介意的话,您可以开始自己的演讲了。”
姚立忽地嗤笑一声,总是挺直的腰板塌了下去,整个人软绵绵地倚靠上沙,如同泄了气的气球。她微抬下巴,双眸迎上华丽的大吊灯,眼神变得迷离。
毫无预兆地,姚立开口说起自己的故事。故事很长,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略显生疏的口音,却字字清晰。
“我原名姚秀凤,就是最土的那几个字。我老家在西川山城,是当年最穷的农村地区。2ooo年,千禧年,是个龙年。我哥就属龙,却是条孬龙。他比我大了整整六岁,家里供到大专毕业,没找着好工作,还坏了手,回家歇了两年。眼见着年纪大了,家里也没盖新房,娶不上婆娘,爸妈都着急。他们想逼我嫁人,收点彩礼钱好给我哥说亲。我不肯,偷了半瓶农药,威胁说要么让我去打工,要么替我收尸。就这么着,我刚满十八岁就离开家南下,成为万千打工妹的一员。我走的时候头也没回,暗自誓,我一定要在大城市里立足,这辈子一定要赚大钱,要出人头地。”
寥寥数语,道尽那个时代农村年轻女性的艰难处境。在姚立的补充叙述中,她的奋斗史显然更为复杂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