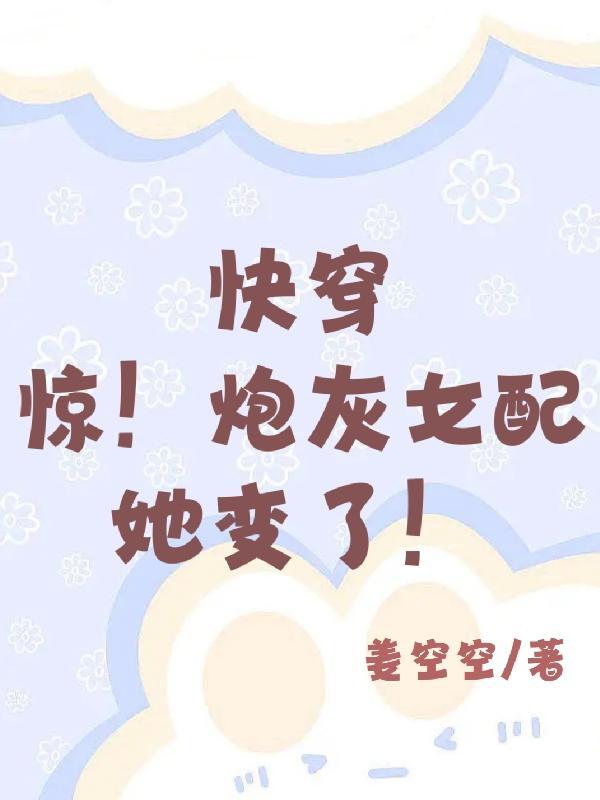车臣小说>美阱之屋在线观看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那肯定不会。这些画像,肯定都是上头专人审查过的,画得不像哪个敢随便贴出来?再说了,如果画得不像,怎么可能抓到人?”
“那倒也是。论理,这么一副外表,走到哪儿都扎眼得很,怎么整整三年了都没抓到人呢?该不会……”
“呸呸呸,别乱说!要我说,柳公子定是找了个好地方躲起来了,或者有什么厉害人愿意把他藏在自家深宅后院里……”
“妇人之见!”旁边有个粗鲁的男声打断了两个女人丰富的想象,“朝廷发了狠要抓的通缉要犯,谁敢私藏?也就你们这些粗浅妇人,看到个清俊小白脸就不知道自家姓什么了,敢有这种大胆想法!”
“切,你管我们怎么想?自己看自己的,谁要跟你这种丑八怪说话?”女人的声音不甘示弱。
“我丑八怪?我看你俩才是丑八怪,还敢对着人家侯爵公子的画像发春,小心被军爷抓去问话!”
男人悻悻然,女人的声音再度响起,木二毛却已听不清他们又吵了些什么,只把目光投向那张新贴出来的通缉画像。
画像虽是简简单单的黑白笔墨,却格外精细传神。
画里的人脸颊上半部轮廓柔和,笔锋走到下颌处又骤然收紧收窄。眉毛浓黑英挺,鼻梁挺翘,一双杏核眼乌黑灵动,唇角含情似笑。如墨的长发在头顶盘成整齐的发髻,令整张脸显得清逸又贵气。
木二毛盯着画像看了半晌,又往旁边的文字看去。
画中人姓柳名舜卿,前平阳侯嫡子,年方二十二,身高约八尺。有知其下落提供可靠线索者,赏金五万;毫发无损活捉此人者,赏金十万。
旁边有个男人“啧啧”感慨:“哎呀,同样是通缉要犯,这价钱可差得海了去了!别说活捉了,我要能有幸知道这位小侯爷的下落,子孙几辈子的生计都不用发愁喽!”
“谁又不想呢?可惜咱天生没那个命。这通缉令前前后后不断翻新,已经贴了三年了,要能抓到,早该抓到了。这位小侯爷真要藏,估计也藏不到咱这穷乡僻壤来。”
“这你可就错了!要想躲过官府的耳目和追捕,藏的地方那自然是越偏僻越好啊!”
“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一会儿赶紧上庙里拜拜,要求也不高,让我能跟这位柳公子打个照面就行。”
“跟菩萨求这个,你也不怕夭寿!”旁边人笑骂道。
木二毛转动眼珠看了身边两个男人一眼,唇角忍不住勾出一缕嘲讽。
几年过去了,那人还是这么一副不依不饶的性子,非得睚眦必报,赶尽杀绝。一个才二十出头、身无所长的孤家寡人,又能威胁到他什么呢?
背着空竹篓赶回秋宁山庄的时候,天已擦黑。守门小厮看见木二毛,笑道:“庄主今儿傍晚回来了,一回来就惦记着找你呢!”
木二毛颔首道过谢,脚步一转,朝着山庄正中的主人房走去。
木垚正在房里指挥下人收拾他带回来的各色物品,听到叩门声,忙过去亲自开门。
门外,木二毛微微躬身,问候道:“木先生,你回来啦?”
“柳公子,快进来坐。”木垚脸上不自觉带出温软和煦的笑意。
木二毛闻言后背一僵,眼睫快速垂下去,整个人顿在门口一动不动。
木垚无奈笑了一下,歉声道:“抱歉,是我的错。一些日子不见,老毛病又犯了。二毛,快进来吧。”
木二毛这才缓步进了主人房。
木垚上下打量他一番,蹙眉道:“你又去采药了?”
木二毛微微笑了一下:“别的营生我也不会,幸得先生教我识得些药草,自然只能靠这个谋生了。”
木垚轻叹一口气,缓缓摇头道:“我都说了多少次,我秋宁山庄虽然鄙陋,也还养得起一个你,你这又是何必?”他盯着对方伤痕斑驳的手背和脚面,心里莫名发酸。
木二毛却淡笑道:“木先生过谦了,秋宁山庄怎会鄙陋?只是,我从前吃够了软弱无能、倚赖别人的苦。今后,无论如何,都要靠一己之力活下去,还请先生成全。”
木垚抿了抿唇,只得点头应承。
木二毛又从衣袋里翻出一个打着补丁的荷包,从里面掏出150钱银子,缓缓递到木垚面前:“这是这月的伙食钱,我先交十天的,等下次卖了药,我再交剩余的。”
木垚盯着木二毛手里只剩不到50钱银子的荷包,沉默半晌,还是抬手收下了。经过无数次交锋,他早已知道,自己拗不过面前这个看上去好脾气的人。
辞别庄主,回到自己房间,木二毛躺在硬床板上,久久无法入眠。
许是今天进城见了那幅越发酷肖的画像,他平静了许久的心底不免泛起层层涟漪。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个春日,想起那位从来都只知骄纵任性的小少爷了。
那原是个极为平常的春日,景色与往年并无不同。
可是,那一天,当前所未有的无能狂怒爆发的那一刻,似乎便已无情宣告,小少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就此终结。
如果时光能回溯,他多想回去告诉那无知无畏的少年,放下执念,放下嗔痴,从今往后,便能少了无数人间苦痛。
可惜,他不能。
所以,那番泥泞难堪,那些心如刀割,就总也无可避免。
【作者有话说】
古风追妻火葬场,非常可爱的柳舜卿小少爷求宝宝们给点评论、收藏鸭()
美人
那是景元十七年三月的一天,中夏都城上洛城里,墙角下和背阴处的积雪早已化尽,桃花和绿柳顺着街巷次第蜿蜒,一直延伸到一处高门大户的内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