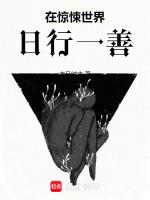车臣小说>古代盗墓复国宝藏 > 第8章 珍藏品(第1页)
第8章 珍藏品(第1页)
太白我愣在原地。
我依稀记得,第一扇门刻字“壶口”,我们遭遇了类似壶口瀑布的机关;第二扇门刻字“沉香”,我们见识了镇墓的沉香木雕龙。那么,第三扇门所刻“太白”,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一扇石门都对应一个墓室或者机关。。。。。。哎徒弟你说,咱们该不会挖到李太白的棺材了吧?”齐师傅在我身后一通胡诌,让我本就发懵的头脑更混乱了。
“胡扯。李白的衣冠冢在安徽呢。再说‘太白’也不一定专指李太白。不要被唐朝这个特殊年代所影响。”我努力回忆,古书里“太白”一词最早是代表长庚星,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太白金星。
“哦——”齐师傅拉长了语调,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那徒弟你的意思是,咱们这回挖到太白金星的棺材了?”
我沉默无语。
我决定跟他绝交十分钟,不说话。
但等众人合力推开第三扇石门,所有人都愣在原地,陪我一起变成了哑巴。
这里,竟然全是陪葬的陶俑!
几乎所有陶俑都是珍贵的唐三彩——那是一种唐朝流行的铅釉彩陶,通常具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最常见的是黄、绿、白,所以被称为“三彩”。
由于存世数量有限,唐三彩也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我们站在门口,粗略一看,就有文官俑、武士俑、男女使者俑,牵狗牵马牵骆驼的使者俑,另有什么杯盘、瓶碗、执壶、釉罐。。。。。。三彩斑斓,遍地开花!
但最让我们震惊的,并不是陶俑的形态之美,而是陶俑的数量之多。
唐朝对随葬品数目有着严格的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陪葬六十件冥器,三品以上则可使用九十件。比如,如果某人仅是七品芝麻官,那绝不可以陪葬九百件冥器,除非他不想要脑袋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讲这种题材的故事会刻意避开唐朝,唐墓里总共就这么多宝贝,少得可怜,限制太多,不方便吹嘘。
可我数数眼前的陶俑,大大小小,别说九十件,真是九百件也有了。
“这要都是真品,再找个好买家,够在京城换十套房了。起床能瞧见故宫的那种。”齐师傅啧啧道。
“想当官,就别想发财。”我烦躁地指指前路,说这座天井换师傅你带路,尽量走快一些。
我目测这第三个天井的占地面积,恐怕比前两座加在一起都要庞大。可是,要按照我们现在的龟速行进,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探索完毕。
更何况,就算我们耗得起,这满地的古董也耗不起。我是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又不是博物馆的隔氧保护罩子,尽管身后三位考古队员一路心急如焚,告诉我这些国宝文物正在快速氧化,我也无能为力。
“遵命,咱们速战速决。”齐师傅答应我,立刻举高腕灯给大家开路,仿佛手持一道耀眼的光剑,切割开暗沉的墓穴。
当一个人走在黑暗的墓道,两旁皆是金玉珍宝。周遭无人,全凭自制。谁都很难抵挡住诱惑。
但齐师傅脚下生风,头也不回。
我看着他的背影,不免产生钦佩与自豪。您瞧瞧,贪财的人还真干不了我们这一行。每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每件文物都是国家宝藏。无论是谁,若是偷偷拿走一件,国家遭受的损失就不可估量。
国宝属于国家,更属于每一个国人。它们理应被妥善保存,或长眠故土,或在博物馆大放光彩,而不是辗转于犯罪分子手里,或被刨出安息的土壤,被迫承受氧化的痛苦;或被锁在非法收藏的柜子里,永不见天日。
很多盗墓贼被金银财宝迷了眼,要么凄惨丧命,与墓穴白骨作陪;要么锒铛入狱,看十年铁窗流泪。以命换钱,以猎奇换刺激,这不叫快乐,更不叫冒险。我不希望任何人重蹈那些可悲盗墓贼的覆辙。
真正的荆棘丛中自在人。
万宝丛中过,寸金不沾身。
我们继续穿过密密麻麻的陶俑群,赫然发现它们同样受到了海水的冲击,东倒西歪。不过,这些陶俑形态各异,高度也参差不齐,甚者居然超过一米。单看这点,说是帝王陵墓都不会觉得奇怪。
“徒弟,看过县志吗?你们西海一千多年前,估计连个渔村也没有吧,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位帝王来?”齐师傅一句话从队伍前面飘来。
我不假思索,说这位户主应该是僭越了吧。
唐朝盛行厚葬之风,虽有法律约束,偶尔也会出现僭越的情况。比如父亲是手握重权的三品唐节度使,偏偏他最宠爱的幼子不幸夭折了,尽管幼子并没有一官半职,但这位父亲还是僭越规格,为他的孩子放置一座只适用于三品以上官员的石墓志。
这种小事一般不会传到朝廷耳朵里。就算真有一些“上书谏者、谤讥市朝者”,朝廷碍于权势,碍于人情,碍于各个方面,大概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位户主僭越得也太夸张了。八成家里是做大买卖的,钱多的没地方烧,全拿来捣鼓后事了。”齐师傅猜测道。
古代商贾地位很低,中唐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里就记载了风尘女子找商贾当接盘侠的常规操作,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但古时的商贾也有不少富可敌国,走南闯北更是无人起疑。再加上唐代海洋贸易繁荣,如果他们真能打通关系,偷偷跑到偏远海滨,建造一座超规格墓葬也不奇怪。
我低头沉思,脑海中也像浪花一样翻滚着各种可能性。
浪花谢幕,浮现出一位富甲天下的海商,他乘坐着一艘朱阁绮户的锦帆楼船,猎长鲸,开天池,泛蓬瀛,穿梭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
他一生与各国商人交易,积累了无数珠宝。我想象那一艘艘满载而归的巨轮,在夕阳余晖下慢慢驶入港口,甲板上堆满异域的珍宝。年迈的商人依旧神采奕奕,手指划过闪耀的明珠丝绸,直指西海波涛,宣告他的埋骨之地。
走着走着,忽然,队伍停住了。
我上前瞧瞧,原来是齐师傅三心二意,竟跟一只陶俑玩闹起来了。
他用手勾住一位青面棕衣判官,一手拨弄着陶俑胸前的琥珀黄色文书,说什么我们是专门保护文物的警察,下墓见您一趟可不容易了,您就在功劳簿上给我们记个三等功吧。三等功就行。
你还有心情玩?都什么时候了!我正准备呵斥他几句。
下一秒,我停下脚步,呆呆看着齐师傅和那位判官陶俑。
怎么啦?齐师傅看向我。
我慢慢地说,其他陶俑都被水冲得东倒西歪,这具陶俑。。。。。。为什么偏偏是站着的?
别赖我啊。这哥们儿本来就是站着的,我可没好心把他扶起来。齐师傅无辜地摊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