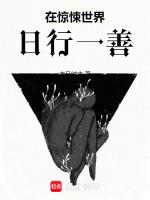车臣小说>宁都县属于哪个省哪个市 > 第79章 警告(第2页)
第79章 警告(第2页)
宁林氏心中一暖,她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也让郎君看到了自己。
宁忠佑心底却冷笑一声,怯弱?
弟妇若是怯弱,那他嫡妻可就是胆小如鼠了。
等诸人散去,宁忠佑漫不经心的把玩着腰上的玉佩,道:“程氏是你杀的。”
连声疑问都没有,竟如此肯定。
宁林氏也知宁忠佑不是个好哄的,既然都如此摆在明面上来问自己,那定是知道了些什么。可她这兄伯……难不成是觉得自己一个女子过于狠毒了?
“兄伯,我……”
“做的太过优柔寡断。”
此言一出,宁林氏愣住,眉头微皱,一副不解的模样。
宁忠佑背过手,傲然道:“留陈琴一张嘴在,又将她卖往别家,终有一日那蠢货反应过来,这件事会成为别家刺向你的一把利刃。若我是你,便将那蠢货灌了哑药卖往最下等的窑子里去,以绝后患。我这人阴毒,绝不会容许自家的把柄落在旁人手中。”
宁忠佑说完就离开,负手而立,如此潇洒。
宁林氏却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不知过了多久,她突然冷笑一声,“这是警告我呢?”
这哪里是在告诉她如何处理陈琴,这明摆着是要吓唬她,若做出任何于宁家有害的事,她的下场自会比陈琴惨上千倍万倍。
宁林氏转身,心中不屑。
可她从来不是什么胆小的女子,既然兄伯有言,那便照做。不仅要做,还要做的更狠,更毒。
宁林氏望着陈琴被人牙子检查着品相,笑着道,“这刁奴可是毒害了她的主子,王婆子觉得她应卖到哪里呢?”
王婆子买卖奴仆多年,自然也听出了这美妇人的弦外之音,当即笑眯眯的道:“名声不好的姑娘不好嫁人,名声不好的奴才自然也是不好出手的。依老身看,这奴才品相不错,卖到窑子里也是能得几两银钱的,只是正经的青楼却是瞧不上她这面皮,只有那下等窑子,去伺候屠夫农户的了。”
陈琴身上不停被婆子摸索,本就挣扎的厉害,闻言愣了一下,出“呜呜”声,挣扎的更为厉害,两个粗使婆子险些按不住她。
宁林氏用帕子掩了掩鼻子,略有些嫌弃,“这陈琴可还是个贞烈的主儿,王婆子不遂她愿将她卖到下等窑子,仔细她一时愤恨咬坏了客人,窑婆要找你赔银子可就不好了。”
王婆子点头哈腰,“娘子说的是,还请娘子放心,窑婆多的是法子惩治不听话的小贱蹄子。至于咬坏客人嘛……老身过些日子给娘子答复,娘子且安心。”
宁林氏手一抬,轻轻搭上春桃的手,动作优雅从容,“那就有劳王婆子了,春香,送客。”
王婆子不愧是老油条,宁林氏不多点明她就知宁林氏是什么意思,不过两日,王婆子就来报说陈琴被窑婆灌了哑药,拔了牙齿和指甲,又悉心“教”了几日,如今听话的不得了。
宁林氏随手放一个荷包在桌子上,“做的不错,赏你的。”
宁甯夜中正在酣睡,迷糊之间听得有人交谈,“这小娃娃太小了,能是吗?”
“管他呢,抓走就是!这么多人质在手,以他们的优柔寡断,就算是顾忌这些女娃娃的性命也不敢对我们如何。”
还未来得及睁眼,宁甯就被人捂了嘴蒙了眼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