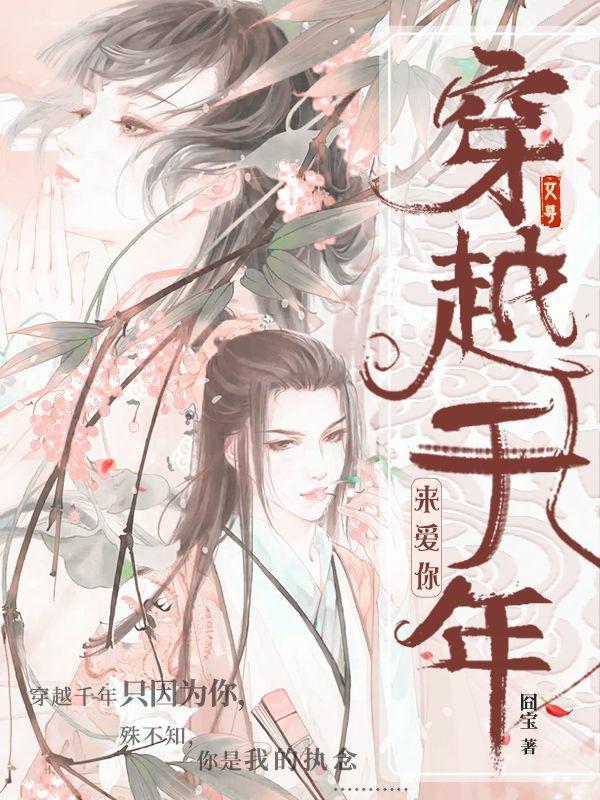车臣小说>不断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全文免费阅读 > 第81頁(第1页)
第81頁(第1页)
沈淮臣難堪極了,攏在袖中的手無意識掐進掌心,整個人坐立難安,宛如凌遲。可即便如此,對容瑄的去向,他始終三緘其口。
過了約莫一盞茶的時間,魏氏逐漸止住哭泣,眼中隱隱帶了自嘲與懇求:「方才哀家在收拾箱籠里的物件,一個人終歸有些寂寞,遠疴若無事,隨哀家一起吧。」
沈淮臣根本找不到理由拒絕。
所謂舊物,大多是這對兄妹兒時穿過的衣裳,戴過的長命鎖,除此之外,沈淮臣還看到了一張宮廷畫像。
古代的人物畫並不似現代那般寫實,比起精細描繪更注重人的神韻,沈淮臣沒法從五官辨認容瑄與容珝,但看得出在鞦韆旁一坐一站的兩個人是快樂的,便也不由自主地勾起唇角。
魏氏看在眼裡,忽地拿出一隻妝匣,裡面盛放的玉佩乍一看是環狀,分開後卻是獨立的兩部分:「這對玉佩名為相見歡,乃是先帝贈我的定情之物,本想著日後再……」
她的話突兀一滯,搖頭笑道:「既然你與永寧有緣,便贈予你吧。」
假如其他人聽了這話,此時再見她吞吞吐吐似有隱情的樣子,怎麼也該忍不住刨根問底了,那時魏氏再將真相據實告知,單憑容瑄看中沈淮臣是好色便於操控才與之成親這點,就足以在兩人心中埋下一根毒刺。
等徹底爆發的那刻,便是兩人分道揚鑣的時候。
奈何魏氏遇見的是沈淮臣。
沈淮臣壓根沒聽出來。
或者說他一直魂游天外,魏氏的話一個字都沒裝進耳朵里,幾番推辭之後皺著臉收下了。
魏氏試探不出深淺,眉心微凝,不著痕跡打了個手勢,立刻有宮人進來稟告說:「太后娘娘,午膳已備妥了。」
魏氏便收起最後一件小衣,含笑問道:「時候不早了,遠疴,一道用過午膳再回府吧。」
面對邀請,沈淮臣依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好在席間有容珝調解氣氛,不至於太過尷尬。
好容易吃了飯,任務倒計時只剩最後十小時。
沈淮臣在系統指引下抄小路來到奉先殿。
晌午,他利用系統的置物功能在容昶的飯盒裡塞了張紙條,上書:[今日申時,偏殿,有要事回稟。]
長時間趕路使沈淮臣的身體持續發出預警,他的度愈來愈慢,必須咬緊齒關拼命催促自己才能抑制住停下休息的本能。
當一次次彎著腰捂住胸口劇烈喘息的時候,沈淮臣耳邊嗡嗡作響,眼前只剩一條通往奉先殿的青磚路,再騰不出精力思考容瑄得知此事該有多麼憤怒與難過了。
待趕到偏殿外,面色已然慘白如紙,汗液浸透裡衣,黏糊糊貼在背上。
萬幸時間卡得剛剛好。
容昶不知拿什麼藉口暫時支開了守衛,沈淮臣擦去額間的淋漓冷汗,拍拍臉頰,努力使氣色看上去紅潤飽滿一些,而後深吸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是你?」
許久未見,容昶保養得宜的髮絲不知不覺白了個徹底,與全天下所有普通老人一樣身形消瘦脊背佝僂,看向沈淮臣的目光陰鷙而又瘋狂:「樹倒猢猻散……想不到,惦記著朕,第一個來見朕的人居然是你。」
「是不是那個婊。子叫你來的,叫你來看朕的笑話?」
容昶上前一步,枯瘦的手指堅如鷹爪,猛然掐上沈淮臣纖白的脖頸,緩緩收緊:「你休想!你們休想……總有一日,朕會把失去的一切奪回來,朕要剝了那個婊。子的皮,將她千刀萬剮!」
「陛下……」
窒息的噁心感如洪水淹沒了他,沈淮臣徒勞地扳動容昶的手指,卻如蜉蝣撼樹,除了在那樹皮般的皮膚上留下幾道白色抓痕外沒有任何用處。
容昶低笑起來,居高臨下地望著他張開的唇瓣,泛紅的眼尾與無意識流出的生理性淚水,像在欣賞一隻垂死掙扎的白天鵝。只要再稍稍用力,便能徹底折斷對方美麗的脖頸。
最好是連翅膀也撕下來,做成標本掛在臥房,這樣才算真的解氣。
【宿主,快念台詞!念台詞啊!】系統急哭了,它不是不想電死容昶,奈何一旦動手,容昶只會更加戒備拒絕合作,到那時誰都承擔不起任務失敗的後果。
台詞……
台詞是……
眼睛有些昏花,腦中混沌,沈淮臣用力咬破舌尖換德片刻清明,掙扎著說道:「陛下,呃……臣會幫助您……臣,願誓死效忠您……」
容昶鬆開手,任由他跌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聽不出情緒地問:「朕憑什麼相信你?」
容昶掐壞了他的聲帶,沈淮臣按著喉嚨,嘗試數次才說出話來,卻再不復往日清亮:「陛下除了信我,別無選擇。」
容昶盯獵物似的盯著他,本想殺他泄憤,突然間改了主意,從靴底取出一枚巴掌大的銀色令牌:「愛卿欲助朕撥亂反正,這樣大的事怎不早說,嘖,瞧瞧,自己人打自己人,還險些丟了命。」
沈淮臣沒吭聲,容昶紆尊降貴地蹲下來,將令牌塞進他手裡拍了拍:「看守東華門的將軍薛儀,昔年受過朕的恩惠,屆時你只需將令牌交給他,他便知道該怎麼做了。」
兩日後便是中秋,中秋佳宴,正是動手的好時機。
至此,事情再無轉機。
沈淮臣將令牌塞入袖中,踉踉蹌蹌出了偏殿。絲毫沒有注意兩道黑影自門外閃過,一人去往太后居住的慈寧殿報信,一人徑直出了宮,找到了容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