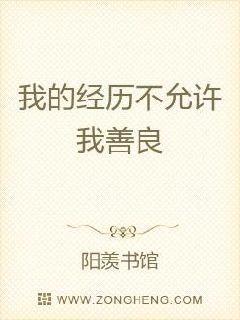车臣小说>锁南枝原文 > 第41章 元宵节(第1页)
第41章 元宵节(第1页)
本该剑拔弩张风起云涌的邑都,却静了下来,李德裕本以为插翅难逃,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决心,可头顶上的那把刀迟迟未落,梗着脖子等死的感觉实在难受,已好几日睡不着了,这日,李德裕晚膳也没用,待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对策。吴氏心中担忧,带着丫鬟提着食盒去了书房。
吴氏将食盒放在书案一角,劝道:“老爷,身体要紧,晚膳多少用一些。”
李德裕心中正是烦躁,拧着眉头不耐烦地挥挥手,反问道:“不是叫你进宫面见谢太后,定下浩儿与那谢家姑娘的亲事吗?为何这么久还没个结果?”
吴氏闻言叹了一口气,道:“拜帖递了几回了,回回都是推脱,说是太后身子不适,不见命妇。”
吴氏似有不甘,又道:“老爷不是瞧不上谢家,不愿与之结亲,如今为何这样心急了?”
李德裕并未将账册一事和盘托出,而是借口道:“如今朝堂局势波诡云谲,不可掉以轻心。谢延光虽不堪大用,可谢太后在宫中。若我们能与之联手,就等于在皇帝身边放了一双眼睛,便多了一重保障!”
吴氏虽不满意唯一的嫡子娶谢家姑娘,可后宅妇人也是知道朝堂的艰险,点点头道:“老爷说得有理,妾身明白轻重,我明日再往康仁宫递帖子求见太后。定将此事办成。”
李德裕点点头,挥挥手叫人退下了。他似乎累得很,双眼闭着,靠在椅背上,呼吸声有些重。李德裕也明白,事到如今实在有些回天乏术。
突然他睁开了眼,眼神有锐利的杀意,咬牙道:“我不能坐以待毙,想要我的命,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把我逼急了,大家同归于尽!”
说着铺开雪白的宣纸,提笔写了起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
天刚擦黑。稚子便提着兔子灯游街来了。小商小贩早早支起了摊,吆喝声不断。生意最好的还是数花灯摊位,各种各样巧思的手工灯笼吸引着人们争相购买。骊水湾热闹非凡。湖面上飘着许多承载着少女情怀的花灯,小小一盏,随波而去。
江映林一手拿着一串糖葫芦,一手手里端着一盏小小的莲花灯,有样学样地也将莲花灯投进湖水中,岸边潮湿,湿了她的裙摆,她也不甚在意,岸边的人越来越多。
江映林本就是偷偷溜出来的,怕叫人认出来,便差绒葵去面具摊上买了一副兔子面具,带上之后显然无所畏惧起来,步伐都轻快许多。
“姑娘刚刚投花灯的时候许了什么愿?”绒葵看她吃得开心,问道。
“还要许愿?”江映林诧异:“我不过瞧着姑娘们都在放花灯,去凑个热闹,居然还可以许愿?现在许还来得及吗?”
绒葵掩嘴笑了,打趣道:“姑娘怕一门心思都在手里的糖葫芦上了。”
“胡说!”江映林自然不肯承认,却又自然地又咬了一口糖葫芦,有些含糊地说道:“愿望嘛,希望母亲再也不要罚我抄书了,那些佛经晦涩难懂,实在难写,手腕现在还疼呢。”江映林说罢还苦着脸揉了揉右手手腕。
绒葵不想打击她,自家小姐性子跳脱,不爱拘束,眼看到了嫁娶的年纪了,夫人恨铁不成钢,自然严厉了些。可姑娘错认的快,犯的更快,这不,罚的书还未抄完,这又偷溜出来了。
“老爷最疼姑娘了,姑娘去老爷那里哭一哭,或许这罚就免了呢?”绒葵也心疼自家小姐,暗暗提醒道。
“爹爹是愿意纵着我玩闹,平时是能说上话的,可母亲若是真动了气,爹爹便只顾着哄母亲去了,哪里还顾得上我。”江映林叹了一口气。
绒葵刚准备开口,就见江映林一步三跳地来到了一个桂花蜜汁莲藕的小摊前面,两眼放光:“现在这个季节居然还有桂花吗?”
“这桂花是奴家去岁十月采摘的,清洗晒干以后储藏在地窖里,趁着今日元宵节做些蜜汁莲藕来卖。”摊主是个中年妇女,看有人来问,连忙兜售道:“这藕刚出锅,最是清甜的时候,姑娘可要来两块?”
江映林点头如捣蒜,又冲绒葵努努嘴,绒葵赶紧上前付了钱。摊主喜笑颜开,麻利地从锅中捞出热气腾腾的蜜汁莲藕,桂花的香甜一下子弥漫开来,叫人食指大动,江映林乖巧地坐在小食桌前,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摊主将莲藕稍稍放凉,提刀切成片状,再浇一勺汤汁,便端了上来。江映林正要动筷,便听得急促的马蹄声,从街尾传来且越来越近。
江映林蹙着眉头瞧着那疾行而来的人和马,路人被吓得纷纷躲避,突然她看到三丈之外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那人背对着她,看不到脸,周边没有旁人,江映林看他似乎想要转动轮椅,却不知为何一步也没有动。
“小心!”江映林大叫一声,丢掉筷子冲了过去。
陈钰川听见声音转头看去,瞧着那飞奔而来的人,那身形有些眼熟,手里的暗器一顿。
就是这一顿,江映林已经冲到眼前,想拉着他的轮椅向旁边退去,却用力过猛,将轮椅拽到。
陈钰川把握不住平衡也从轮椅中跌出,两人纷纷倒在路边,在江映林要磕到头的那一瞬间陈钰川还伸手过去,垫在她的脑袋下面,道了一句:“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