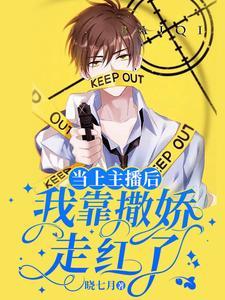车臣小说>围困的英文 > 第2章(第3页)
第2章(第3页)
我惊叫着从噩梦中醒过来,睁开眼睛的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异常。
漆黑的背景里,一双深邃的黑眼睛从正上方直直地盯着我看,我被他吓得呼吸都要停摆,第一反应就是去摸枕头底下的大白狗腿。
虽说我很快就认出这是自己的枕边人,但他比我更快察觉到我的意图,死死地扣着我的手不许我移动,用力大到我怀疑我的腕骨会被他硬生生捏碎。这种姿势下,我和他离得很近,鼻尖挨着鼻尖,嘴唇贴着嘴唇。他身上有很好闻的味道,凉凉的柔柔的,我深吸两口才意识不是他身上凉,而到我浑身都是热汗,连呼吸都是烫的。
“小哥,你……”我喘着气把头侧向另一边,试图说点什么缓和一下紧绷的气氛,“你放开点,你这弄得我有点痛。”
他听话地放轻了力道却没有完全松开,细长有力的手指蛇一样插进我指缝间,和我十指交扣。
饶是再迟钝的人也该注意到他今晚的情绪很不对劲。和他背着我去的神秘的目的地有关吗?我被热意搅得一团浆糊的大脑断断续续地想。除了蛇沼里他刚失忆那会,我从未在地上亲眼见过他如此激烈失态的情绪。
我胡思乱想着,他自顾自低下头,把脸埋在我的肩颈处,梢擦过我的皮肤,嘴唇贴着我的颈子慢慢往下,像是倾听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很热,空调开着不应该这么热,但事实就是我后背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都是汗的味道有什么好闻的,我后知后觉地感到不好意思想要推开他,可我跟他在力量上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又是这么个不好使力的别扭姿势,推了两下反而把他拉得更近。
颈子是我们这种人的命门,一般人我绝对不允许他靠得这么近。他的呼吸很绵长,气息又很轻,撩得我喉咙深处一阵阵的痒。
尽管什么狼狈的样子都被他看过了,我还是拼了命地不想在他面前失态,我屏住呼吸,等待这阵冲动消退。他停下摸索,支起身子看我,我自诩对他情绪了若指掌,看得出他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又是一阵咳嗽,我努力把咳嗽声吞咽下去,没想到却刺激得反胃起来。
不知是哪个点惹到了他,他看起来心情更加恶劣。
“呼吸。”他低声说,“咳出来。”
他把我抱起来,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失去了人为施加的那层阻力,我咳得撕心裂肺,他的手从拍改成自上而下的抚摸,一下下帮我顺气。我靠着他的手臂,房间里除了雨声就只有我粗重嘶哑的喘息。
“你刚在看什么?我就是又做噩梦了。”我故作轻松地趁机提出自己想了许久的事情,“实在不行还是分两床睡吧?”
我睡眠差,他又睡得浅,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人同样的警觉心很重,像这样硬是勉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摇摇头,“没关系。”
我看着他没太多表情的脸,一时间内心十分复杂。
责任。他认为他对我有责任。a1pha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同伴的责任。
我自认是个很不着调的人,但即使是我也未曾想到道上叱咤风云的哑巴张有朝一日会因为上了我这个过命的兄弟被逼婚。
张家和天授,过去的几百年来,他已经背负了太多,我曾以为我能把他从这样的宿命中解放出来,到最后我也成为了这些人的一员。
一瞬间我突然非常的难过,我看进他漆黑如点墨般的瞳孔里,“小哥,两年,最多两年……”
“嗯?”他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常见的迷茫。
我没有再往下说,他似乎也不执著从我这里等到一个结果。
他的生命太漫长了,漫长到我一眼看不到尽头,所以从一开始,时间的意义于我们就是不对等的。
我被他困在手臂构建的狭小空间,而他也被这场雨困住了。大雨将我们围困在这个地方,兴许是黑暗中人能够有勇气做一些青天白日下不敢做的事情,我纵容了自己的私心,抬起手环抱住他的肩膀,然后把自己拉向他温暖的躯体。
在我尚还年轻些的时候,我对他有过很多极端的念头,它们大多炽烈如火、锐利如刀,既伤人也伤己,而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就想陪在他的身边,至少此刻……我希望我还能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他悲伤难过时给予他分毫慰藉。
第四章
按照一开始的计划,我们打算领完证就回福建,好巧不巧盘口那边出了点问题,需要我亲自去一趟。
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碎催,真正的硬骨头没几块,闷油瓶坚持要和我一起去,让我好好体会了一把有人撑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