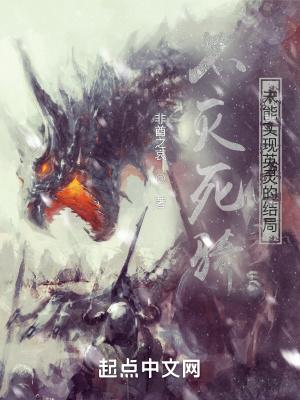车臣小说>怜怜 在线阅读 > 第25章 这一次她坚决不会再妥协(第2页)
第25章 这一次她坚决不会再妥协(第2页)
这口气从裴景修中状元那天就一直提着,直到今天,她终于把话一股脑说出口,这口气也终于可以畅快地呼出来。
虽然很难,但她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没说出来之前,她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说出来之后,现其实也没那么难。
她想起小叔教她的话,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自己的东西要自己争取。
小叔是对的,虽然她目前还没争取成功,但硬气的感觉确实蛮痛快的。
她坐在窗前,没有流泪,也没有惶恐,视线落在面前那两本册子上,头一次觉得“训”“诫”这两个字是如此的刺眼。
它们就像两张看不见的网,把世间所有的女子都网在其中,薄薄的两本册子,就划定了女人一生该走的路。
凭什么?
不过是几张纸而已,凭什么就能让所有的女人心甘情愿被它束缚?
不抄,她不抄,这一次,她坚决不会再向裴景修妥协。
她倒要看看,裴景修能不能把她饿死在房里?nbsp;这段时间,穗和真的变了许多,他都快有点不认识她了。
他收起眼中的温柔,表情变得严肃而冷沉:“穗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近来事忙,疏忽了对你的教导,你就把女人家的三从四德都忘了吗?
你前几天和母亲争辩,就已经违背了女诫女训,我念在你受了委屈的份上没有指正,不承想你却越的往歪路上走,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
他越说越严厉,从书案上拿起两本册子拍在穗和面前:“这几天你就不要出门了,好好把《女诫》《女训》各抄十遍,等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再放你出来。”
说完不等穗和反驳,起身大步出了门,把穗和反锁在了房里。
紧接着,他又去了阎氏那边,对阎氏说:“穗和这几日闭门思过,小叔的饭菜让玉珠去做,小叔若要问起,就说穗和不舒服休息几天。”
“为什么是我?”裴玉珠不满地嘟起嘴,晃着阎氏的手撒娇,“母亲,我不想去,小叔那么难伺候,我做的饭他肯定不喜欢的。”
“你就不能用心做吗?”裴景修厉声道,“你好歹跟着穗和学了三年,样样都只学个皮毛,你若连小叔都服侍不好,就别妄想在京城寻个好人家,别人家的公婆不会比小叔更好伺候。”
阎氏现在一门心思扑在和国公府联姻上面,对小女儿也没了耐心:“你哥说得对,你想今后在婆家过得顺心,就先在你小叔那里练练手,过了你小叔那关,将来嫁去婆家我也能放心些。”
裴玉珠很害怕兄长火的样子,一看母亲也不站在自己这边,只悻悻道:“那好吧,我去就是了,可小叔若问穗和什么病,我该怎么说?”
“就说是女儿家每月都会有的。”裴景修说,“小叔没那么闲,你这么一说他就不会多问了。”
穗和被锁在了房里,并不觉得难过,反倒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从裴景修中状元那天就一直提着,直到今天,她终于把话一股脑说出口,这口气也终于可以畅快地呼出来。
虽然很难,但她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没说出来之前,她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说出来之后,现其实也没那么难。
她想起小叔教她的话,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自己的东西要自己争取。
小叔是对的,虽然她目前还没争取成功,但硬气的感觉确实蛮痛快的。
她坐在窗前,没有流泪,也没有惶恐,视线落在面前那两本册子上,头一次觉得“训”“诫”这两个字是如此的刺眼。
它们就像两张看不见的网,把世间所有的女子都网在其中,薄薄的两本册子,就划定了女人一生该走的路。
凭什么?
不过是几张纸而已,凭什么就能让所有的女人心甘情愿被它束缚?
不抄,她不抄,这一次,她坚决不会再向裴景修妥协。
她倒要看看,裴景修能不能把她饿死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