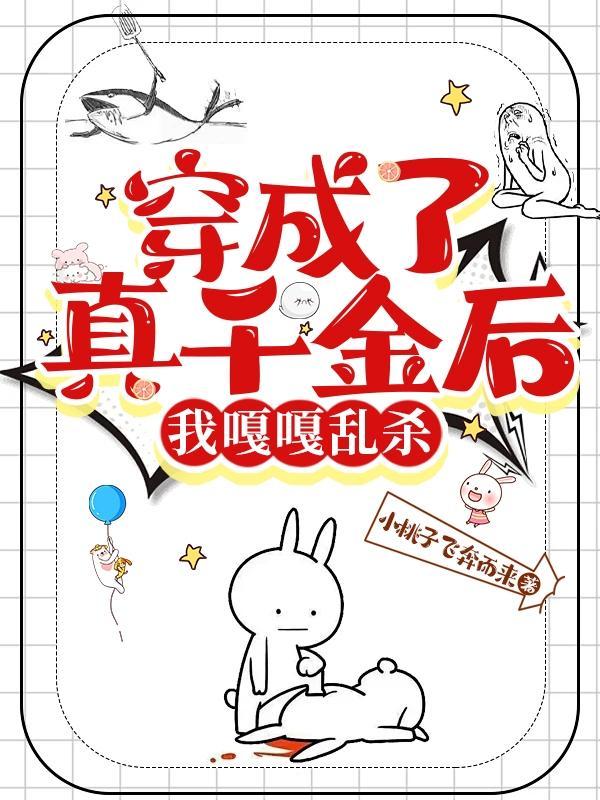车臣小说>暗夜天堂 韩剧在线观看 > 第11页(第1页)
第11页(第1页)
“丽子姐走之前特别交待我你一定会来的,她让我等你过来时把这个交给你。”美代子从手包中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
“”男人脸上的笑容很慢很慢地收敛。
“是关于通口先生的消息。”女人把信递了过去,“丽子姐是在婚礼当天知道的,她现在正在法国渡蜜月。”
“”史部忽然静静地泛起一个笑容,放下怀里的小孩走到女人面前接过信:
“内容——我大概已经猜到了。”
“丽子姐说如果你以后还要来店里就让我帮你,但是她不希望你出事。”美代子用转述的语气冷淡的说,史部微笑着点点头,
“我知道了。”
“妈咪”站在一旁的男孩忽然轻轻地拽了拽女人的裙摆,美代子低下头看了看孩子,伸手从吧台的里侧拿出一罐罐汁的水果樱桃。
“一会儿我会帮你打开的,但是你要记住,这种甜水淹过的东西不可以多吃啊!”
“小孩都喜欢吃这种东西吗?”史部突然像是很感兴趣的低下头望着抱着罐头仰着头也望着他的男孩。
“大概只要是小孩都不会讨厌这种甜的发腻的东西吧!”美代子冷淡的回答。“是——吗?”史部拉长声音轻声说。
“”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男人忽然蹲下身笑笑地望着眨着大眼睛的男孩很认真的轻声问:
“可以把那个送给我吗?虽然现在没与可以交换的东西,但是以后我一定会回报你的。”
“跟一个孩子不用那么正式的说话吧,如果你想要那个的话拿走就是了。”女人古怪地望着男人。
“可以吗?”史部依然十分认真的望着男孩,过了一会儿,孩子一言不发地把手中的罐头递到了他手中。
“我会再来的!”史部站起身把罐头揣进衣服里,笑着向女人挥了挥手从正门走出了店。
“你果然还是个不轻易说‘再见’的家伙。”女人突然很轻地自语似的说,一抹自嘲式的笑慢慢浮现在女人无瑕的面颊上:
“你这样是因为你在说再见时已经做好了不会‘再见’的准备了吗?你还是一个那么让人讨厌的家伙呀!”
(他最他讨厌,最讨厌说谎的人了!)
通口椿人把几乎全部都剩下的一锅米饭恨恨地一口气倒进垃圾带里。
(那个男人一定是憋不住又到哪个女人的家里去了,只有他才会傻到听信那个男人的话真的把米饭多做了出来,那个男人现在一定躺在什么不正经的女人床上偷笑吧,反正就是他自己笨罢了!)
门的锁忽然响了一下,椿人的手仿佛做错事正被抓住一样莫名奇妙的抖了一下,男孩用力地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手指紧紧地抓住手中的塑料袋。
“你已经吃过了吗?”男人在门口甩下鞋子,光着脚迈进只有八块塌塌米大小的屋子,原本就很小的屋子因为男人的进入而变得更加狭窄。
椿人像是想要抗拒什么似的挺直了身体别过头硬声说:“你又没有要我等你。”
“既然你已经吃过了我就放心了!”史部像是没有听到男孩声音中挑衅一样满不在乎地点着头说,忽然他像刚刚才想了什么似的从衣兜里一罐罐头,蹲下身静静地放在男孩面前。
“这个是给你的。”
“”男孩一语不发地回过头望着摆在地上的樱桃罐头,过了一会儿面无表情的静静地问:“出了什么事情吗?”
“”史部用一种奇异的表情歪过脑袋,轻轻地皱了皱眉。
“该不会是你出去赌钱把所有家当全部输光了,让我以后只能露宿街头了吧?”椿人嘲弄似的抬起头望向满脸困惑的男人。
“你为什么那么想住在这里呢?”史部望着他慢慢问。“这和你没有关系吧!”
男孩冷淡而且漠然地回答,史部看了男孩一会儿忽然轻轻地问:“你那么想见你的父亲吗?”
“”椿人一瞬不瞬地望着男人的脸,原本没什么表情的脸上很慢很慢地闪过一丝近乎冰冷的嘲弄,然后慢慢地,男孩别过头用一种执拗的语气平静而冷淡的说:
“那个男人已经死了吧!”“”
有那么一瞬间椿人以为那个高大得像头熊的家伙会把慢慢举起的手落在他身上,他已经做好了被打翻在地的准备,毕竟以一种陌不相关的口吻谈论自己的父亲的人是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想到那个男人把抬起的手慢慢遮在了自己的脸上,然后很大滴的眼泪一滴一滴地从那骨节粗大的大手下流了下来,一下一下地砸在地上。
“”椿人轻咬住自己的嘴唇看着男人粗大的喉头无声的上下滚动着,那只粗大手掌下原本就很削瘦的脸颊更加用力的紧绷起来,一种奇异的感觉慢慢在椿人的心底模糊的弥散开。
“你到底到底在哭什么呀!”男孩忽然拧紧眉头,带着一种奇异的困惑紧绷着声音大声问。“”
“你不要、不要再哭了好不好?”椿人咬了咬嘴唇试图忽略心中涌起的那份莫名的焦燥,用一种不耐的语气很大声地对男人说。
“”屋子里的灯泡忽然闪了闪,一下子灭了下去,屋子里安静得没有任何声音,椿人烦燥地动了一下,安静了一会儿男孩突然带着一种近乎恐慌的困惑摸索着把手伸向应该就在跟前的男人:
“喂,现在还不到停电的时间吧!”“”
黑暗中,一只粗大的手突然抓住了椿人伸到前面的手臂,一双瘦长的手臂十分用力地抱住了男孩纤细的身体。
“”
没有任何的声音,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男人仿佛想把所有东西都和头一起埋进男孩的衣服里一样,很紧很紧地抱住他的身体里。
(是我在发抖吗?)男孩困惑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种潮湿滚烫的东西从被男人紧贴住的地方慢慢渗进椿人的身体。
(发抖的难道是那个男人吗?)
椿人怔怔地看着那个埋在他胸前的巨大的头颅,在他自己发觉以前,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像要安抚一个被人丢弃了的受了伤的动物一样,把手轻轻地抚上男人潮湿而且散发着灼热温度的头。
过了很久,男孩才胸口从不知名的紧窒中找到自己的一丝声音,他犹豫着,用很轻很轻的声音低声说:
“可以不要再哭了吗?”
“大概是老天弄错了,其实你才应该是那个男人的儿子吧”椿人淡淡地轻声说着,慢慢地把头转向别处。
(老天为什么要弄错这件事呢?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所有人都会变得很开心吧?)
(如果眼前这个男人是那个男人的孩子,那么他的母亲一定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人,即使爱上了那个男人也不会被自命高尚的家人像对待垃圾一样赶出家门,更不会在死了以后依然被当作污秽一样做为嘲弄的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