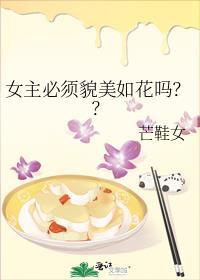车臣小说>明月台赋全文免费阅读TXT > 第54章(第2页)
第54章(第2页)
“为何?”我骇然失声。
伽莱静默片刻,含糊道:“蛮夷女人诞下的子嗣,自然是鄙陋粗劣,一时得势便想颠覆万明、胡作非为。”
蛮夷?我心里悄悄哂了声,若以渊国为正统,他们万明人不同样身处蛮夷之地?如今倒是互相鄙薄起来。殊不知驱使各部相互征伐、彼此牵制历来是大渊皇室的制衡之策,只不过到了我那位皇叔时,渊国国力衰退,难以再作壁上观,以黄雀之策,得渔翁之利。
“若要说继承大统,想来还是身份尊贵者为上佳。”我假作无意,接了话。
略显犀利的目光落在脸侧,伽莱似乎是在细瞧着我,斟酌这句话的意味。
论身份,他身为嫡长子,母亲又是巫族公主,自然尊贵无比。若非伽牧伪造字迹诓骗我那位皇叔,这王位十有八九要落在他身上。伽莱虽有偃旗息鼓之意,骨子里到底还带着巫族人的倨傲,我几番耳旁风吹过,便足以让他的狼子野心死灰复燃。
然而这次,我却在他的眼中感受到一股恶寒。
伽莱沉下脸,推着我的轮椅往无人处去。半旧的大门合上,震得梁上积年陈灰飞扬如絮。
“近日我常想,你何时变得这样聪明起来。”他俯下身,大片阴翳如展翅俯冲的猎隼般落下来,“又觉得你蠢,藏也藏不住那股聪明劲儿。”
我一惊,复又飞快压下眼底慌张,笑道:“我常读房中那些书,自然是会变聪明的。”
伽莱扳住我的下巴,似笑非笑地搐了下嘴角,吐出三个字来。
“沈鹤眠。”
一瞬间,我寒毛倒竖。
若我没记错,这是饮药后他次喊我的本名。他自始至终为我精心设计了念卿的身份,企图让我忘却真正的自己,却在这一刻将身份亲手撕裂。
“你究竟有没有喝那碗药?”他的笑因面上斜划过右眼的可怖刀疤而显得格外狰狞,口中吐出切齿之词的同时,布满厚茧的手已然扣在了我的脖颈之上。
似乎只要我说出“没有”两个字,纤细的颈子就会在下一刻被捏碎。
这也不奇怪,他从前似乎就是这样对我的。扼住脖颈,以示我的性命之脆弱,迫使伽萨向他服软。
只是如今伽萨不在了,我也不似从前慌张无措,反倒还能风轻云淡地喘两口气,对上他那只闪着盈盈绿光的狼目。
我眨着圆瞳,问道:“什么药?”
我眼下失了忆,哪里知道什么药呢?
他的目光越凛冽,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似的,讽笑道:“那碗被你泼在地毯上的蛊药,孵出的蛊虫将踏床蚕食蛀空。若不是阉奴方才无意踏上致使踏床崩塌,快马加鞭前来告知,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等本事。”
“沈鹤眠,”伽莱恨得咬牙切齿,“我给过你活路。”
我看着他怒的模样,心里反倒没由来地平静,甚至带了一丝玩笑:“所以,你如今要杀我?”
颈上的力道骤然加重,窒息感从颈间窜上颅脑,我不自觉垂下眼睑,又努力抬起,道:“你只知道我不曾喝药,却不知我被蛊虫折磨得头痛欲裂、生不如死,如今也算解脱。”
“它们在我脑中爬动、啮噬,叫我痛不欲生,又将我囚于轮椅之上不能自主,这便是你给我的活路。走到底,不过还是死路一条。”
想起从前在雪地里同他说起伽宁,伽莱眼角眉梢是有几分动容的,足可见其并非全然铁石心肠之人。哪怕是花言巧语地蓄意诓骗,只要能取得他的信任,我便能更好地使一出离间计。
他的手指在我颈上松了三分,露出一瞬的犹豫,又顷刻握紧了。
还差一点。
我抬手软弱无力地攀上他的腕,继而再道:“我还记得你说累……”
闻言,伽莱恼羞成怒地双手施力,几乎将我顷刻扼死在轮椅之上。我脑中一片空白,咕哝道:“我便……舍不得喝那药了。”
生死挣扎之际,所说的话最为真心,哪怕这“真心”是我私下筹谋练习了无数次的。
“你说什么?”眼前虽然还是模糊一片,伽莱的声音已经飘至耳侧。
我张了张嘴,瘫软在轮椅上。他扶住我的肩前后摇晃,又托住我的脸,掺着几分迫切地一字一句清晰问道:“你说什么?”
“我没有别的依靠了,我只有你。”我松松拽着他的袖子,眼神迷离地吐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