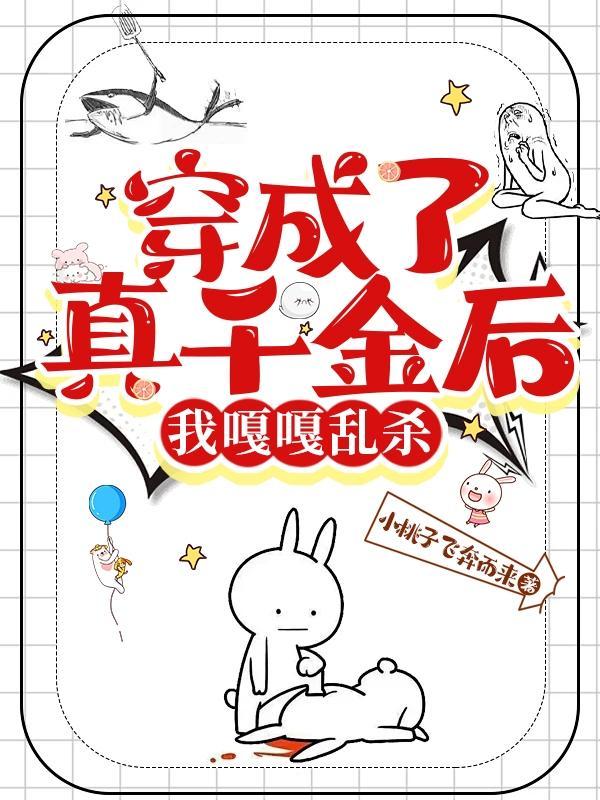车臣小说>凯恩舰哗变的真相 > 2梅middot温(第2页)
2梅middot温(第2页)
“我想也是。那个红头发的呢?”
“啊——她叫什么名字?”
“梅温。”业主说,斜眼看着威利,可能是因为燃着的烟头离他的脸太贴近了。
有时候说出一个名字会在一个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被人高声喊出来似的。这种感觉常常被证明是幻觉。总之,威利被“梅温”二字的发声震动了。他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的身段如何?”威利回答道。
业主被烟呛了一下,把剩下的一点烟头在烟缸里压灭“你还不如问菲鱼多少钱一斤呢,那跟她的身段有什么关系?我问的是你对她的演唱有什么看法。”
“哦,我喜欢莫扎特,”威利含糊地说“但——”
“她是便宜货。”丹尼斯先生心里盘算着说。
“便宜货?”威利生气了。
“薪金,普林斯顿,如果她不会把治安警察引来,那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不知道。也许那首莫扎特的东西会给这里带来令人愉快的新气象——名声、档次、魅力。但它也有可能像一枚臭气弹把这里的客人全吓跑——咱们且去听听她怎样唱简单点的东西。”
梅温的亲爱的苏比前面唱爵士乐唱得要好——可能是因为它不是插在莫扎特乐曲的框架里的,没有那么多的手的、牙的、臀部的动作,南方口音也没那么重了。
“你的代理人是谁,亲爱的——比尔曼斯菲尔德?”丹尼斯先生问。
“马蒂鲁宾。”梅温说话时紧张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能礼拜一就开始吗?”
“怎么不能?”姑娘喘着气说。
“定了,领她四处看看,普林斯顿。”丹尼斯先生说完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威利基思和梅温单独处在那些假棕榈叶与椰子果中间。
“祝贺你。”威利伸出手说。那姑娘用她那温暖、坚实的小手紧紧地和他握了一下。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去,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