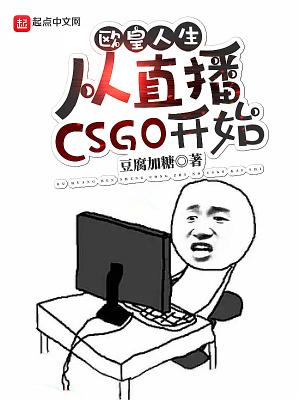车臣小说>谋色己晚 > 第2页(第1页)
第2页(第1页)
“有母后足矣,别人怎样看儿臣,又干儿臣何事?”黎洇声音略低,微垂的眼中涌起一层淡漠,很快便敛了起来。
“洇儿,母后这次叫你来是为了跟你说一件正事儿。”薛皇后捏了捏黎洇滑润的小脸,笑道。
黎洇幽黑的眼睛眨了两下,等着她接下来的话,岂料薛皇后只是慈笑地着看她,并未置一词。
黎洇娇气地哼了哼,轻轻地摇着她的胳膊,“母后,你倒是赶紧说啊,儿臣的胃口都给您吊开了,每回都这样,非让儿臣求着你,外人都说是母后惯着儿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儿臣惯着母后。”
薛皇后听了这话,呵地一声,“小丫头长大了,敢跟母后绕口舌了。”
“那母后到底是说与不说,不说的话儿臣来说罢,儿臣瞧中了母后的那对缀玉玲珑珰,不如母后送给儿臣怎样?”黎洇一口气说完,眼巴巴地瞅着她,目光朝远处的首饰盒子瞟了瞟。
“贼丫头,敢情你是早相中了母后的那对耳珰子,本宫道你今日怎的来得这么勤快。”薛皇后佯装不悦地挪开她缠着自己的手。
“母后好生小气,父皇平儿都是怎么哄的?”黎洇低声嘟囔一句。
“不悦”的薛皇后还是急忙忙地命婢女妙玉取来了自己的首饰盒,往黎洇身边一摊,“看上哪件了只管拿,当母后不晓得你有那收集宝贝儿的怪癖。”说完,无奈又纵容地瞪了她一眼。
黎洇抿了抿嘴,“瞧母后说的,儿臣确实喜欢珠光宝气的东西,但也不是见着谁的都觊觎。这些都是父皇赏赐母后的,儿臣可不敢要。”虽这般说道,小手还是动作迅速地将首饰盒里的缀玉玲珑珰拣了出来,收进了自个儿怀里。
薛皇后心里暗笑,想起稍后要说的事,脸色渐转凝重。
“洇儿,再过不久你便及笄了。以后携驸马入住公主府,母后再不能日日看到你。但是,只要洇儿想母后和父皇了,随时都能入宫探望。”似觉得自己的语调沉重了些,薛皇后笑了声,摸了摸她低垂的脑袋,“公主府也快完工,府邸便是上回母后给你指的那一处,离皇城不远,周遭环境也算清幽。洇儿想去瞧瞧的话,下回母后陪你同去。”
黎洇一只手还在首饰盒里翻搅,听闻这话,动作一顿,慢慢垂下了头,有了自己的公主府就意味着她成人了,也该选驸马了。可是,她一点儿不想出宫,更不想离开母后。
“日子过得真快,儿臣本来还想着多陪陪母后。”黎洇嘟嘴道,将首饰盒阖住递给一边的宫女妙玉。无意间瞟过去的一眼叫妙玉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埋下了头,淡漠、警告、狠意,似一把利剑直刺入她心底。
“母后最舍不得的便是你了,挑驸马也一定会给你挑个最好的。”薛皇后宠溺地将她往怀里一揽,“你父皇的意思是,此次琼琅宴会上让你自个儿也多留意着些,尤其是今年殿试出彩的新贵们。”
黎洇哦了一声,“儿臣晓得了。”
三月殿试结束后不久,敬仁帝会同往年一样,在琼琅殿里举办洗沐宴,以殿试前三甲为首,会试前二十名紧随其后,相继入殿参与琼琅殿宴,朝廷官员七品以上皆可参加,从四品以上更可携其家眷,命妇和小姐们由薛皇后于隔着珠帘的另一侧接待。
听闻今年殿试折桂的状元郎韩沐诩郎艳独绝、风姿翩翩,黎洇双眼微微眯了眯,随即又恢复了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薛皇后见她兴趣缺缺,咦了一声,打趣道:“吾儿不是最喜欢长相俊美之人么,如今有如此良机当场逡巡一番,怎的一副蔫蔫的模样?”
黎洇细眉一挑,煞有介事地回道:“皮囊再美也不及里面装着一个干净的灵魂,国师上回去祥云寺讲道时,我恰记住了这一句。”
薛皇后微微皱眉,肃然提醒道,“国师不喜人打搅,你日后少去叨扰他。”
黎洇撅了撅嘴,“母后可冤枉儿臣了,国师大人长什么样子儿臣都不晓得,祥云寺讲道时,京都中的命妇和官小姐们都去了,可是给女子们讲道时,国师周围挂着纱帐子,众人根本观不到真人面貌。除此之外,我甚少叨扰国师,只是上次臣心中有几个不解之惑,遣下人去绝尘宫问了问,没想到国师大人一一作答了。”
说及这国师木子影,却是个大有来头的。大昭国并非一直风调雨顺,五年前,京都里干涸一片,连续两年未雨,田地皴裂,颗粒无收。敬仁帝隔上四五天便要祭天求雨,可惜一直未见成效。周太师及朝中诸臣齐齐上奏,恳求迁都,奈何敬仁帝不忍弃下京都之地。君臣僵持之际,敬仁帝命人广贴告示,召集天下能人异士,望有大师能除此大难。敬仁帝本只抱着微渺希望,没想到最后竟等来了一个自告奋勇的世外之人。
此人名唤木子影,虽着一身朴素白衣,容貌却是俊美无铸,敬仁帝一时惊为天人,设为上宾。设坛作法之后,天上果降大雨,惊煞众人。这事从此成为一段传奇,而此人亦被敬仁帝数次挽留,终于皇城里的一处行宫住下,后此处行宫被他自命为绝尘宫,整座宫和这个人便似这偌大沉浮暗涌之中的一波清水,干净而让人不敢亵渎。敬仁帝奉其为大昭国的第一位国师,虽无实权,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受尊崇。
“若非你父皇执意留下国师,国师早已浪迹天涯,广施天下。一个仙儿似的人被拘束在这小小一方皇宫里,你父皇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委实不妥。”薛皇后叹了口气道。
“不是仙人也被众人夸成仙儿了。”黎洇撇撇嘴,目光绽放几许晶亮,显然被勾起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