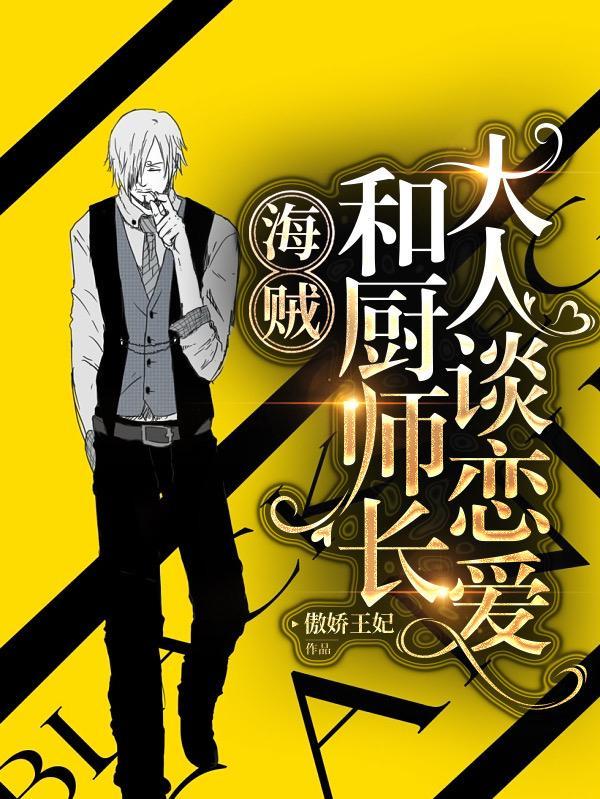车臣小说>传闻不实娱乐圈免费阅读 > 第41頁(第1页)
第41頁(第1页)
「侯爺忘了,我從來不是什麼君子。」羲姱笑了一聲,「事到如今木已成舟,侯爺與其在我這白費唇舌,不如想想摺子,儘快與我撇清關係。」
傅行深沉沉看她一眼,「你就這樣想我?」
「盡忠職守,侯爺高義。」不知怎的,那目光像是塊烙鐵,倏地燙了羲姱一下,她垂了眼,輕聲道,「我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場對峙後是罕見的沉默,傅行深連夜差人將她送出府的時候,羲姱還在想,以傅行深行事之手段,要想獨善其身實在太過容易。
她畢竟只是個妾。
萬幸她只是個妾。
臨行前,她坐在陳設乾淨的馬車裡,聽見傅行深似乎在車外叫了一聲自己的名字。
羲姱沒有應,車簾的一角輕輕動了動,傅行深的眉眼從帘子縫隙里一晃而過。他像是想說些什麼,最後卻只落成一句輕飄飄的珍重。
珍重,羲姱心道。
若能死在你手裡,倒也算是一種圓滿。
可她沒有被送進宮裡,侯府的車夫馬不停蹄,把她送到了一處北境邊上的村落。
傅行深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這個偏僻的鄉壤置了處小宅,倒是清淨。她在鎮裡與世隔絕地待了一陣,沒等來自己的問罪書,倒等來了一封長信。
這信原本是送不出來的。
傅行深估計是想把它付之一炬,可他離開得匆忙,沒料到風把未燒完的信,從火盆里吹了出來,又被傅行深的親信撿到,誤當作傳訊送了出來。幾經輾轉,才到了羲姱手裡。
羲姱至此方知,那碗苦得要死的湯藥,根本不是什麼毒藥,而是傅行深千辛萬苦求來的,醫治她舊疾的良方。原來傅行深之前所做種種,不過是企圖在攘權奪利的朝堂上,在小皇帝日漸膨脹的野心下,護她餘生周全。
她早該明白的。
答案在相處的細微處,在隱晦的話語裡,已被說過千百次。只是那時的羲姱,滿眼都是兩國和平,對傅行深更是防備到了極致,恨不得把他的每一份好意,往最壞的那處想,哪裡看得到,他一早就全然交付的真心。
信的末尾,是句被火舌吞掉的半句詩,又或者執筆者本意就是擱淺於此。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心若有所嚮往,何懼道阻且長。
戰場上多少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朝堂里多少次明槍暗箭,都沒教她如此慌亂過。羲姱顧不上傅行深親信的阻攔,奪了馬就往都城趕。
可是已經太晚了。
她不眠不休趕到王宮時,傅行深早已死於亂箭之下。
他未殮的屍身,就是南國主君特意為她設下的陷阱。那也是神女羲姱——
在凡世里的最後一個劫難。
聶遠初讀劇本的時候就覺得,凡塵這一世的結局就該配一場大雪。雪覆落宮牆古蹟,就如他們遮掩了一生,直至死亡也沒能說出的心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