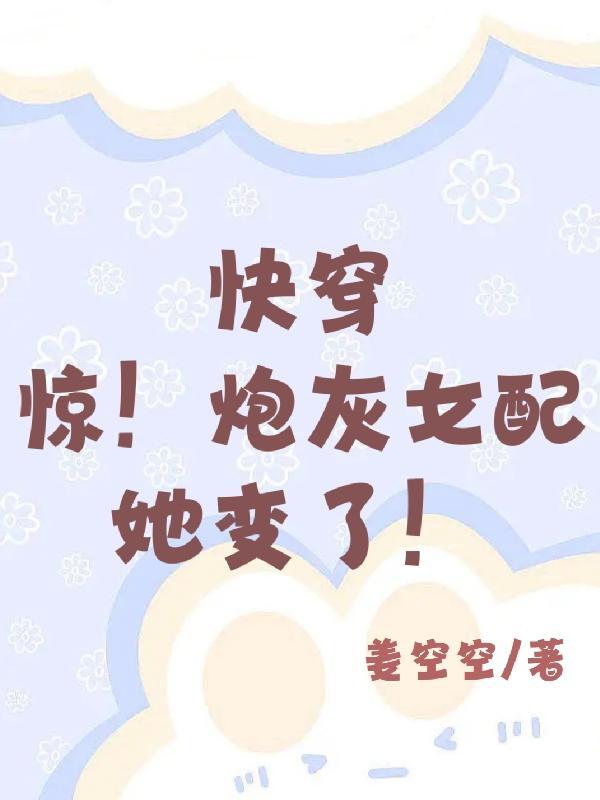车臣小说>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太医这才摸着一把雪白的山羊胡,继续道:“唯有一处,薛美人怀胎三月,按理来说,正是食欲不振的时候,然薛美人却食欲格外强盛,几乎到了一日五餐的地步。”
画钩在一侧为他们掌灯。她年岁小,薛婉樱有妊的时候还未曾伺候在薛婉樱身边,因而对女子孕事所知并不多,听到太医面色沉重,煞有介事地说起薛美人多食之事,不由微微的“咦”了一声。
涂壁较画钩年长,向来比她稳重,见此不由瞪了她一眼,示意她噤声。
一直安静无言的薛婉樱却突然开口,轻声道:“画钩,你想说些什么?”
薛婉樱生得很白,灯火流连中看去,更觉她肌肤莹白如玉。
画钩听到她的话,绞着手中的帕子,有些局促:“奴婢只是想起,从前邻家便有一个媳妇,因着孕中受补太过,胎儿太大,最后难产了,一尸两命的。”
画钩的话一出来,涂壁立刻变了脸色,呵斥她道:“你又胡说些什么?”
这话若是被有心人听去了,难免觉得画钩是在诅咒薛美人,画钩也反应过来,一时脸上有些悻悻的。
薛婉樱却在沉默了一阵后,从案几后起身,示意画钩将脉案收起,又对一旁的涂壁轻声道:“你明日就去甘露殿,告诉灵均的傅母,给贵人进补,须有得宜的尺度,不可一昧贪多。”
涂壁从不质疑薛婉樱的任何决议。
皇后是永远不会有错的。在一众的各有弱处、缺点,劣迹斑斑的凡人中,只有皇后永远公正、仁爱,且美丽,宛若神女。
--
送走太医,听着殿中水钟一下一下地吞吐流水,薛婉樱才意识到原来已经夜过二更。窗外星织如漏,皎月暗无痕,暮春时节,杜鹃掠过海棠树,在庭阶处抛下落花。芳草萋萋,宫人每日晨起洒扫庭院,草绿却仍然从阶下一直延绵到了院中。
水钟之水循环往复,沙漏之沙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不知何处为起点,不知何处为终点,不知今日较昨日有何分别,不知此刻与下一刻有何差处。一如——她的人生,又或者说,深宫中所有女人的人生,薛婉樱突然想到。
也许姨母周太后说得不错,她并不适合深宫禁苑,甚至可能,也不适合任何男人的后院。
薛婉樱十六岁成为天子的东宫妃,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里,她先是侍奉先皇和两宫太后,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儿媳,甚至先皇仙逝前,因为担忧出身低微,行为粗鄙的高太后会仗着天子生母的身份为难她,还不忘严厉告诫天子:“婉樱乃我家佳妇,小子不可轻慢。”
而后又成为了一个贤惠到几乎无可指责的妻子。
世人都说,薛皇后宽容大度,友爱宫嫔,宽待庶子,大有长孙皇后的母仪之德,甚至连薛婉樱的母亲周夫人都曾几次三番暗中敲打她,唯恐她为了贤名,反倒误了己身。
可薛婉樱就只是觉得无趣。
争无趣、斗无趣,费尽心思去讨好她的丈夫更无趣。
太久了,久到她甚至已经想不起少年时和兄弟们一同打马球时鲜衣怒马的快意;也忘记了年少读书时当众和先生争辩古今时的酣畅淋漓。
薛婉樱成了薛皇后,先是一个皇后,而后是天子的妻子,再之后还是太子和公主的母亲,在层层的身份之后,薛婉樱本人已经不再重要了,于是她也就将自己深深地藏起,直至最终只剩一层温柔的画皮。然而在今夜,画皮深处的薛婉樱却突然开始叫嚣:“不,不是的。你首先是薛婉樱。”
可薛婉樱是谁?
抛却中宫的冠冕,薛家女儿的体面,薛婉樱本人还剩下什么?
薛婉樱突然一阵气闷,屏退宫人,独自走出丽正殿,向九曲廊桥走去。
流水迢迢,从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蜿蜒而下,流入矮渠。中夜生寒,薛婉樱沿着九曲廊桥一路行至湖心小筑的时候,掌心已然不复在殿中时的温暖,随着春夜,染上了薄薄的凉意。她一边揉搓着自己的掌心,一边朝亭子里走去。湖岸边立着的宫灯乍一眼看去,明晃晃的,像一轮耀眼的明月,但隔着曲折,照到亭子里,剩下的也只剩下了一圈模糊的光影。
一直到在长石椅上坐下,薛婉樱才意识到身边坐着一个人。
甄弱衣靠在石椅上,偏过脸眯着眼看她,淡紫色的襦裙,前襟开得很低,露出了胸前一大片皎洁的肌肤,过了有那么一会儿,也许是终于看出身边的人是谁,甄弱衣一笑:“娘娘。”
并没有行礼。若是陆贤妃见到了,难免又要生出一番波折,但薛婉樱却无心在这样一个中夜,追究过多的繁文缛节,尽管她身上大多的矜持仪度,都来自于此。
薛婉樱也笑了,温柔、雍和。甄弱衣恍惚间想起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一句同薛皇后有关的话:沐明月清辉,浸春风微露。春夜的寒风吹到甄弱衣脸上,大氅上的狐狸毛领子替她挡了一下,倒也不觉得冷。她听到薛皇后轻声问她:“大晚上的,怎么不在殿中待着?”
甄弱衣笑了,反问道:“娘娘怎么不在殿中待着?”
薛婉樱微微一愣,终于正色来看她,不知过去了有没有一炷香的辰光,她才听到薛皇后再次开口,很轻很轻:“闷得慌。”
是丽正殿闷得慌,还是宫城闷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