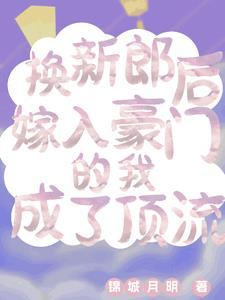车臣小说>残暴鳏夫他嗜血无情免费阅读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药熬好了,南澈用勺子给怀安喂下,怀安不肯喝,他嘴巴紧闭,喂进去多少洒出来多少。
醉春殿外有侍卫看守,殿内却只有南澈,在接连几口都被怀安无意识吐出后,南澈丢了药勺,那些畏缩怯懦的姿态从他身上消失。
单看南澈的长相,是有一些吓人的,他俊美,但透着薄情寡义盛气凌人的味道。
眼皮是单的,唇瓣是薄的,鼻梁高挺,下颌锋锐,一颗艳丽的“奴”字宛若红色小痣缀在他的眼尾,在每一次的对视里,好似盛开到颓靡的毒罂粟,牢牢攥取人心,勾魂摄魄。
这样的人不会成为谁的春梦对象,真梦见了,只会惊恐这玉面罗煞是否会掐住自己的脖颈,吻痕覆盖的瞬间,也是死亡来临之时。
南澈冷漠的注视怀安几秒,而后捏住怀安的下颌,逼迫他张开嘴巴,发苦的黑色草药灌下去,怀安的喉咙被迫吞咽,来不及吞咽的黑色药汁滑过怀安的脖颈,丑陋的印记玷污雪一样的白。
南澈不在意这人金枝玉叶,动作粗暴,只管将药灌下去。
他吐息阴冷,“皇上,你应该谢谢你那不忠不义的爹,给你留了保命符,否则此刻我喂给皇上的,便是穿肠烂肚的毒药。”
章程嘱咐过,怀安的身体过于虚弱,如若南澈想将这人在世上留久一点,套出兵符下落,怀安的身体便不能再受一点折损。
本已到了强弩之末。
南澈得守着这麻烦精退热,不多时章程开的药便起了效果,怀安开始起热汗,他闭着眼眸感觉到难受,南澈拿了三床被褥压在他身上,怀安感觉到热的同时也感觉到呼吸困难。
他的手臂不自觉伸出被子,南澈当即将怀安的手塞了回去,维持不过片刻,怀安的脚伸了出来,赤白的玉足乱踢。
南澈的脸越来越黑,他没见过这样麻烦的人。
分明都生病了,半点不知安分。
他给了这个废物皇帝活的余地,偏生这麻烦精非要同他唱反调。
他的耐心即将消磨殆尽,南澈闭眼又睁开,他额头的青筋绷起,手握住怀安的玉足,将其塞了回去。
怀安的额头出了些许汗,苍白的面容此刻被胭脂一样的红晕染,鬓角的发丝粘黏,破碎的美感淋漓尽致。
怀安不吃这一套,他咬牙威胁,“你再敢往外伸,我废了你的双手双脚,将你制成人彘。”
怀安听不见这些威胁,他感觉到自己仿若置身于撒哈拉大沙漠,高热的天气要将他晒成猫饼,他费力的想要走出去,千辛万苦看见一处绿洲,他想要探入溪水得一口凉。
却有怪物守着这溪水,一次一次将他驱逐出去。
怀安不信邪,他非要打败这怪物。
在南澈数不清第几次帮怀安盖好被子,怀安不过三秒钟,伸出手,“啪——”得一声,一巴掌稳稳当当落在南澈的脸上。
南澈维持着被扇脸的姿势过了数秒钟,他的脸没有动,深黑的眼珠子先平移转动过来,盯着扇他的那只细瘦苍白的右手,他的头缓慢转过来。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想了多少种床上病弱美人的死法。
这样漂亮的手脚,最合适用来做藏品了。
南澈握紧袖口里的刀,下一秒,南澈面无表情的抽掉了自己的腰带。
病弱皇上假太监4
怀安生得瘦,背部单薄好若一片难承蹂躏的白纸。
南澈皱着眉,万般嫌恶的用被子将怀安卷成春卷,继而用四肢圈住这春卷。
怀安热得厉害,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泼墨似的长睫被沾湿,亮晶晶的汗珠挂在他的白里透红的两腮。
他不似染了高热,倒似在香软的酒里被浸泡到烂醉。
南澈从未仔细看过这张脸。
起初是觉得一个迟早会死的人,他无需去记住。
后来,这忽视由怀安的残暴和羞辱,催化成浅淡的恨意。
南澈薄情、寡义。
他心如死水,装着至高无上的权势,除却高位,不为任何存在起半分波澜。
想要这样一个人的爱与恨,同下十八层地狱并无区别。
怀安当他不记恨是善,根本不知自己招惹了一个怎样的怪物。
睡过一晚,怀安的头脑昏热好了些许,他身子不舒服,汗湿的里衣黏哒哒的裹在他的皮肤上。
怀安欲起床,他的手脚挣扎不得,乌眸半睁,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夜里竟将自己给卷了起来。
此刻在床上和蚕蛹相差无差。
折腾半天,软被散开一些,怀安半只玉足点在地上,里衣斜斜坠在他的腰腹间,层层堆叠的布料好似盛放的白花。
南澈躬身进来,瞧见这一幕,他的视线在怀安白皙皮肉上覆着一两秒,而后像是看不会动弹的死物般,眼中无波澜,头颅垂下去,嗓音捏得尖细。
“皇上,晏丞相在御书房候着您,说有要事相商。”
怀安眼眸撩起,冬日冷,他这身子受不得这样的冻,但这古代的衣服他着实不明白,他的眼眸水亮亮的,哑着嗓子道,“朕想要洗澡。”
“皇上,不可,御医吩咐奴才,您病愈前,沾不得水。”
怀安僵持,半晌,南澈去接了热水,他双手拿着白帕子,跪在怀安面前,“奴才帮您擦一擦。”
醉春殿的殿门在白日里紧闭,若不是皇上后宫并无妃嫔,怕是要不了半刻,便会有艳色床帐之事传出。
怀安的长睫轻颤,这身子皮肤娇气,沾染着烫意的手帕一过,皮肤便落了红。
他没有被人这样伺候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