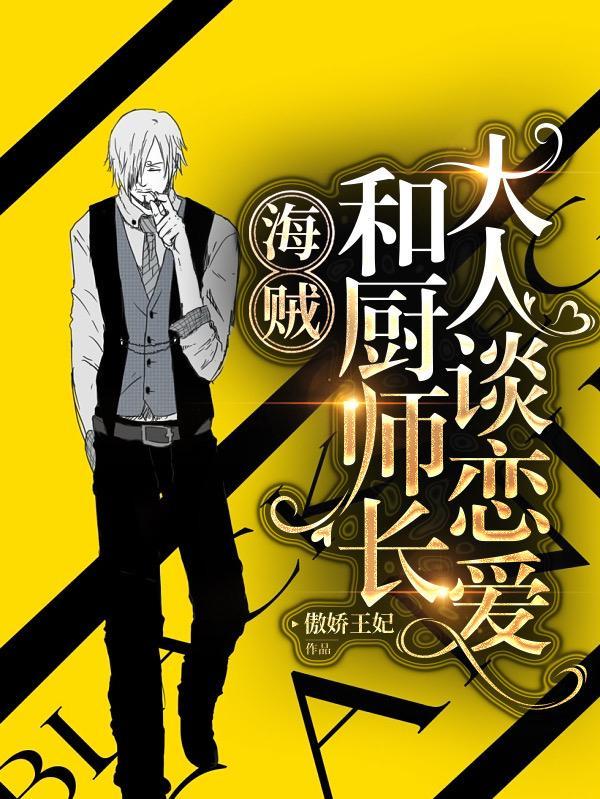车臣小说>死对头穿成我的猫by草履免费阅读 > 第58章(第3页)
第58章(第3页)
“不。”谢松亭固执地摇头,“就差一点了,我要说完。”
毕京歌半蹲着看他,“为什么那么着急要今天说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我不想……”谢松亭痛苦地说,“我不想过年也被这些困扰了,年前都说完吧,我想……我想至少今年过个好年,明年他……不一定在这了。毕老师,行吗?”
“好,我会听。”
谢松亭接过她递来的纸,把纸团抓在手里。
纸团湿得很快。
汗浸的。
谢松亭被绊倒,起不来,在沙土里坐下,看了猫一会儿。
“你怎么没猫陪。”
没有猫回应他。
但他仍在说。
“我也没人陪。”
“我和你聊聊天。你妈妈呢。”
“你妈妈不在啊,好巧,我妈妈也不在。”
“你没有爸爸了,好巧,我也没有了。”
谢松亭把它埋了,连着活蛆一起。
他走上桥,站在桥边崭新的护栏上,手一摸,掌心里全是灰尘。
他看着江面,心想,来这这么久,他还没看过这里的早晨。
今天看一看。
谢松亭从昏黑的夜站到蓝幕渐起,柱光外透,突然想起。
今天星期一。
该上早读了。
他手里没有书,向下看只看到自己全是血的拖鞋,念道。
“我爸死了。”
他像在很快地背诵。
“谢广昌死了,他不是我爸,那谁是。李云岚活着,她不是我妈,那谁是。我是谁?我是谢松亭,我叫这个名字吗,我本来是谁,谁又是我。”
“我渴了,”他突然说,“我要下去喝水,我好渴。”
“我好渴,我好渴,我好渴,我好渴……”
他的渴意漫上来,思维涨大到一定程度时竟然是热的,他逐渐暖热了栏杆,终于看到冬日的太阳。
河岸来的风将刘海向后吹拂,露出他柔软的睫眼。眼睛被刘海挡住很久,被风一吹,有些想流泪。
晨光很薄,没什么暖意,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