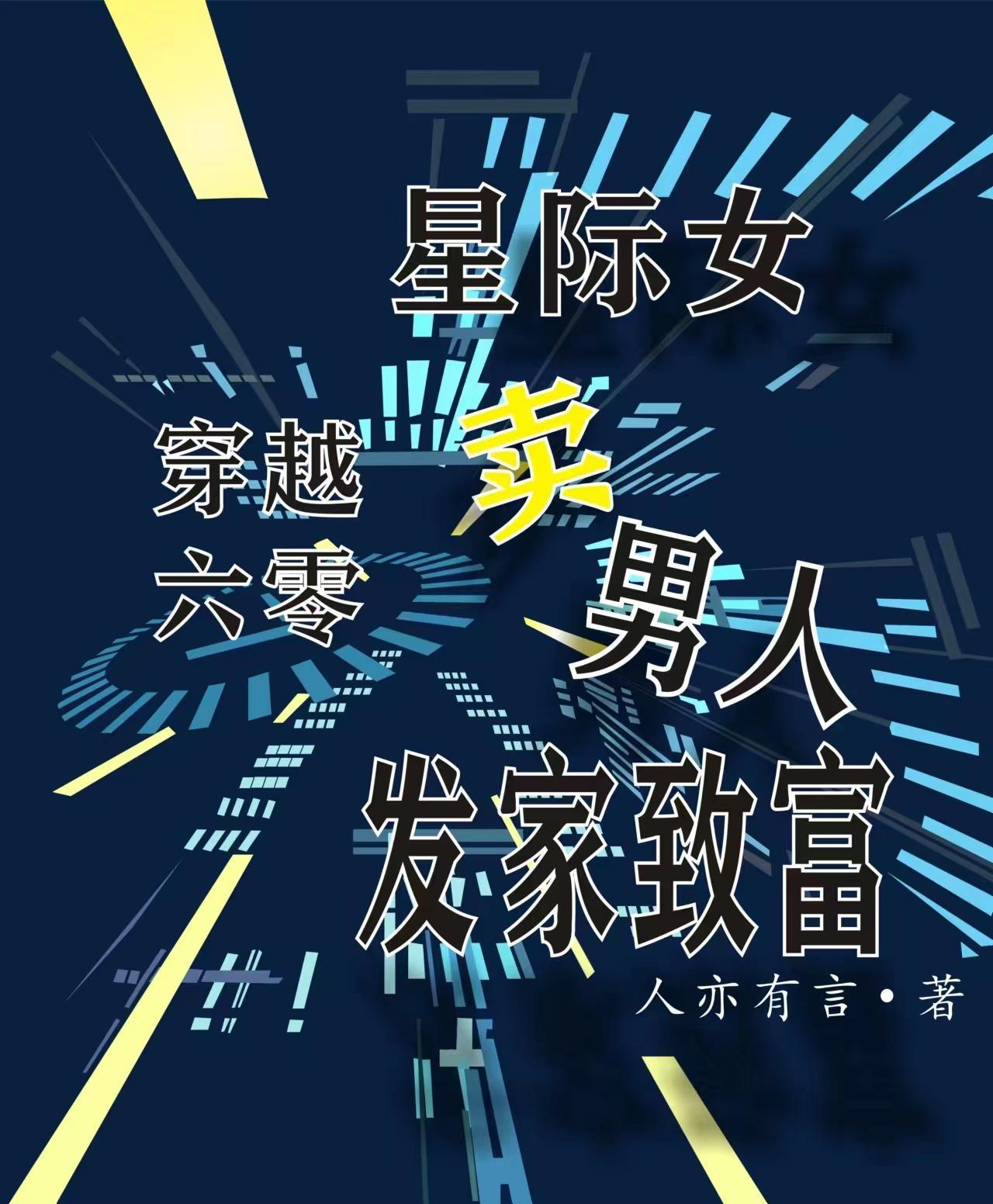车臣小说>感念师友 > 北大三窟(第1页)
北大三窟(第1页)
北大“三窟”
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而是先后三个“定居”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25楼的都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25楼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进21楼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9座,每3座成一品字形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3层,共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1950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了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12平方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一般都是碌架床),一张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是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21楼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19楼去解决。(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虹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在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是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三分之一在19、20或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北京市委常委),等等,当初都是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21楼住了三年,到1986年,搬到畅春园51楼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畅春园在北大西门对过,东是蔚秀园,西是承泽园,连片都是北大家属宿舍区。畅春园可是个有来历的地方。据说清代这里是皇家园林别墅,有诗称“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可见此地当时水系发达,秀润富贵。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见西洋传教士,听讲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知识。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门马路边遗存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也快要湮没在灯红酒绿与车水马龙之中了。1980年代初北大在畅春园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90平米左右,三房一厅,当时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当资历的教授或者领导才能入住。为了满足部分年轻教工需要,在畅春园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楼,绿色铁皮外墙,5层,共一百多间,每间15平米,比21楼要大一些。我决定搬去畅春园51楼,不因为这里房子稍大,而是为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户口,不用再借用煤气本。
毕竟都是筒子楼,这里和21楼没有多大差别,也是公共厕所,也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间厨房。房子还是很不够用,女儿要做作业,我就没有地方写字了。那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非常紧张,家里挤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内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51楼东边新建了北大二附中,当时中学的操场还没有围墙,我常常一个人进去散步,一边构思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那时“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论作发表,我的学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几年打下的。51楼的居民比21楼要杂一些,各个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如刘伟(经济学家,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曾毅(人口学家)都是邻居,我在这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里还有难忘的风景。我们住房靠南,居然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往外观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劳作和变换的景色。后来,稻田改成了农贸市场,再后来,农贸市场又改成了公园,那时我们已经离开畅春园。偶尔路过51楼跟前,想象自己还站在三层的阳台上朝外观望,看到的公园虽然漂亮,可是不会有稻田那样富于生命的变化,也没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还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绪有关吧。
后来我又搬到镜春园82号,那是1988年冬天。
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镜春园在北大校园的北部,东侧是五四操场,西侧是鸣鹤园和塞克勒博物馆,南边紧靠有名的未名湖。这里原为圆明园的附属园子之一,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和珅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和珅被治罪,园子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据史料记载,昔日镜春园有多组建筑群,中为歇山顶殿堂七楹,前廊后厦,东西附属配殿与别院,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飞楼杰阁,朱舍丹书,甚为壮观。(据焦熊《北京西郊宅园记》)后历沧桑之变,皇家庭院多化为断壁残垣,不过也还可以找到某些遗迹。过去常见到有清华建筑系学生来这里寻觅旧物,写生作画。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人还从残破旧建筑的屋顶发现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教员宿舍,包括孙楷第、唐辟黄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50年代之后成为北京大学宿舍区,不过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盖,成一个个大杂院。其中比较完整的院落,一处是76号,原为王瑶教授寓所(曾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馆,现为北大基金会所在);另一处就是我搬进的镜春园82号。
这个小院坐北朝南,院墙虎皮石垒砌,两进,正北和东、西各有一厢房,院内两棵古柏,一丛青竹,再进去,后院还有几间平房,十分幽静。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著名小说家和红学专家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后来让出东厢,住进了古典文学家陈贻焮教授。再后来是“文革”,吴先生被赶出院门,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别给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陈贻焮教授年岁大了,嫌这里冬天阴冷,于1988年搬到朗润园楼房住,而我则接替陈先生,住进82号东屋。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厅可以作书房,一条过道连接两个小房间,还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这一年我42岁,终于熬到有一个“有厕所的家”了。
我对新居很满意,一是院子相对独立,书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欢晚上绕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邻居关系融洽,也很安全,我们的窗门没有加任何防盗设施,晚上不锁门也不要紧,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四是这里离76号王瑶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聆教。在未名湖畔镜春园82号
寓所门前(1988年)
缺点是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买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东奔西跑准备,把蜂窝煤买来摞到屋檐下,得全家总动员。搬来不久就装上了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装机费很贵,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确实有点奢侈。我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用篱笆隔离,种过月季、芍药等许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阴,不会侍候,总长不好。唯独有一年我和妻子从圆明园找来菊花种子,第二年秋天就满院出彩,香气袭人,过客都被吸引进来观看。院子里那丛竹子是陈贻焮先生手栽,我特别费心维护,不时还从厨房里接出水管浇水,春天等候竹笋冒出,是一乐事。陈贻焮先生显然对82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杜甫评传》这本大书,就诞生于此。搬出之后,陈先生常回来看看。还在院墙外边,就开始大声呼叫“老温老温”,推开柴门,进来就坐,聊天喝茶。因为离学生宿舍区近,学生来访也很频繁,无须电话预约,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镜春园一住就是十三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经历了北大的许多变迁,我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接待师友,有艰难、辛苦也有欢乐。这里留下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前不久我陪台湾来的龚鹏程先生去过镜春园,82号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拆迁办”。从门缝往里看,我住过的东厢檐下煤炉还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经枯萎凋残。据说82号以东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报纸上还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保留燕园老建筑。但最终还是要拆迁的。我一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是2001年冬天搬出镜春园,到蓝旗营小区的。小区在清华南边,是北大、清华共有的教师公寓。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汇在“三窟”之中了。
200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