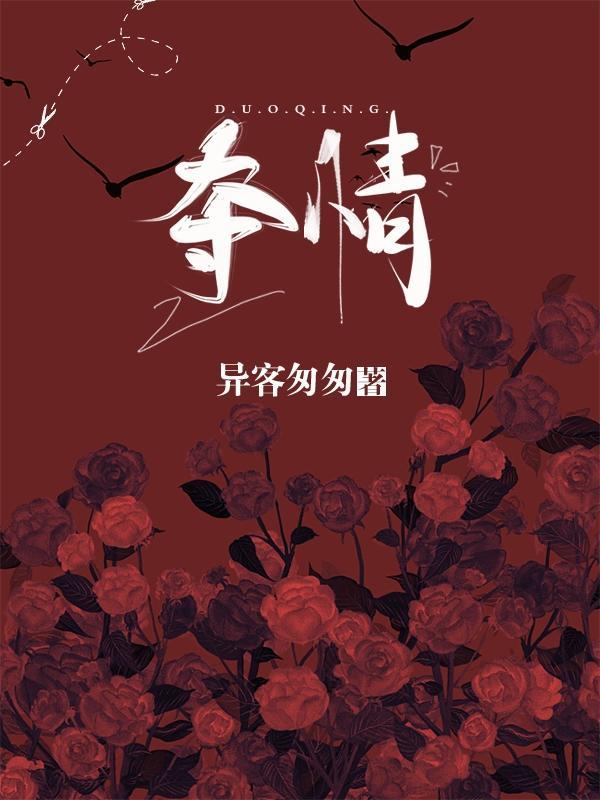车臣小说>朝闻道刘慈欣经典语录 > 第187章(第2页)
第187章(第2页)
齐珩一声轻嗤,道:“姑母也只会说是旁人欠姑母的,从不曾说是姑母欠旁人的。”
“何其荒谬。”齐珩面若冷霜地一字一字道来。
“你懂什么!”
齐令月霎时便红了双目,只觉心头酸涩,委屈至极,她双目盈泪,面容狰狞道:“你,你一个傀儡子,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都是他们,是他们逼我的!如果崔家愿意放过她,放过我,我又何尝会如此。”齐令月扯着袖子,悲声宣泄自己的委屈与怒气。
齐珩一愣,复而道:“可你已借了先帝的手报复崔家,何必要牵连那么多无辜之人?”
“你不懂!”
“既入漩涡,谈何脱身?”齐令月含泪苦笑道。
这条路,是他们推着她选的。
齐令月兀自笑了起来,只是面颊上还挂着泪水,面容十分狰狞可怖,齐珩双唇翕动,并未言语。
“齐明之,我和你不一样。”
“我生在立政殿,长在紫宸殿。”
“父兄疼爱我,母亲亦挂念我。我本该就是这尊贵之人,我也本该是那满怀冰雪之人。”齐令月蓦然落下两行清泪。
“我也说过,我也做过,我也想为民请命。”
“可是他们不让。”
“自儿时起,兄长庸懦,碌碌无为,不堪储贰之位。而我不同,上至天子,下到内侍,这紫宸殿里里外外,哪个人不是称颂我,我的老师,也是你的老师,他最满意我这个学生了。”
“可尽管满意,他也不让我读你们男儿看的书,我神情欢愉地捧着那本《贞观政要》去寻太傅,可太傅告诉我。”
“《贞观政要》,非公主事也。”
恰如世人所说类同,“才藻,非女子事也。”
齐令月渐渐平静下来,她看着袖袍上的泪痕轻声道:“公主该做的,便是会填词、会吟赋,识得诗礼侍奉父兄,做个光鲜亮丽的金丝雀,如此,便已不负公主之名。”
“高宗知晓此事,将那本《贞观政要》在我眼前慢慢焚毁,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静静地呆坐在那里。”
高宗抱着她,轻轻抬手,那本书便已化为灰烬,任风吹散。
她呆滞原地,久久未回神,待她缓过神来,便知随风而去的,不仅是那残书余灰,还有她常常宣之于口的青云之志。
彼时,她六岁。
“齐明之,你也该明白手中无权柄的滋味。”
“我的姨母,知我心的人,就这般冤死在丽景门,你让我如何不怒、不怨、不恨?”
齐珩道:“有冤自有律治,那也不该是你害人的借口。”
“可不害他们,我便保不住自己!”
“律?”齐令月仿若听了天大的笑话般,她扬首朗声大笑。
“齐明之你不懂,你不懂这个王朝对女子的偏见,女子无权,便只能如蒲苇般将自身全然牵系于夫君一人,女子弄权更为不易,我若想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便只能被迫去害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