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小说>古早主攻第一人称 > 第九章陛下尝到了小鹤的眼泪蛋是对的预警和预告(第5页)
第九章陛下尝到了小鹤的眼泪蛋是对的预警和预告(第5页)
其实也挺好的,陆氏将领都在战场上生生死死,我可以给她封个王,把她弄去北疆镇守,顺便清理一下那里的官吏。
唯一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给女子封王的例子,我一想到不得不和朝臣僵持,就觉得头大。
我对江知鹤说:“至少得封侯。”
“封侯?”他看起来有些震惊,随即又笑道,“自古以来,未曾有女子封侯拜相,只怕朝臣不许、天下非议。”
我静静地抱着他,想了想,说:“论功行赏,不可拘于男女。乾坤并健,阴阳合德,始能成事。”
“朝臣是朕之臣子,更是天下之朝臣。国土之万民,四成为女,六成为男,男子可为,女子未必不可为。”
一瞬间,我觉得江知鹤眉眼柔和下来了,看我的眼神都有些温柔,我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只能感受到他柔柔地贴近我的胸口。
“陛下乃天下之君王,生该如此,运该如此,陛下之意乃是天意,天意怎可违,微臣有一计,可叫陛下如愿。”
我忽略他对我吹的彩虹屁,揽着他纤细的腰身往上抱了抱,防止他滑下去,捏起他瘦的有些骨相明显的下巴,“你倒是快说。”
江知鹤被我从我的怀里挖出来,他清凌凌地起身,走到一旁的案牍前,对着我笑了笑,开始研磨。
因为我们两个私下相处的时候,我不喜欢有旁人在身侧,总让我有一种被窥探私生活的不适感,所以侍从被我赶出去了,现在江知鹤只能自己侍弄笔墨。
他以前就尤善书法,是夫子最喜欢夸的那种人,此时他身着官服,端坐于案前,眉目清秀,面似冠玉,身着红袍绣云,腰系玉带,足蹬锦履。
执笔蘸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他或许生来应是白衣卿相,奈何沦落至此,虽风骨犹存,却玉碎山倾。
我也不想躺着,就起身凑过去替他接着研墨,伸手将墨块放在墨盘中,加了点水,然后用墨杵在墨盘中搅拌研墨。
他一看我动手,眉头就皱起来了。
“微臣惶恐,怎敢劳烦陛下。”
我摆了摆手:“你动脑,朕动手,合理分工。”
他见我已经动作,便不再说什么,只是提笔落墨,画出三方之势。
“前朝党争严重,党争之弊,乃士大夫之失德。科举制兴,士大夫权势渐重,排武人、霸朝堂,自成派系,各怀私欲,竞逐权位,此乃劣根性作祟。利益之集团成,各有所图,皆欲自保,致使斗争加剧。”
“陛下应知,今日朝中之势分三方,文为一方,武为一方,宦臣一方。宦臣为陛下手中鹰犬,文武为朝之栋梁。”
“今朝以武掌权,武将势大,以陆氏为首,以陛下马首是瞻,然文武自古不和,文臣之中,以清贵之首沈太傅为首。”
“沈太傅年过半百,子女具逝,膝下无人,只有一个孙女沈无双,才学不输男子,前日,刑部立案,沈氏女以故意杀人罪入狱。”
我一听,来了兴趣:“故意杀人?”
江知鹤点点头:“据说,其未婚夫礼部尚书之子袁英,酒后欲猥亵于她,此女性烈,挣扎之中,将其推入寒江湖,救上来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
他话已至此,不必多言,我就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朕要去主持公道,抓其软肋,收服沈太傅?”
他摇摇头,“陛下莫急,要真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才算是雪中送炭,效果才最好。”
32
说着说着,他又被我抱在怀里了。
我觉得很神奇,江知鹤总是在任何时刻都十分吸引我,就好像鲜花理所当然地吸引蝴蝶一样。
他被我抱得歪歪扭扭,提笔写的字也看着委委屈屈地,扭得厉害。
“陛下,”他无奈地推推我,“莫要如此。”
我不肯,偏偏要扒拉着他。
见状他倒是颇为纵容,继续说,“自古女子无权,陛下可敲砖引玉,先为沈无双免罪,再赐官‘提文’,掌史书传记,投一回问路之石,文臣必歌颂陛下功德,后趁势封许娇妗爵位,文武皆不敢拦。”
“陛下,恩威并施方可翻云覆雨,此局定要拿人开刀才能杀鸡儆猴,”江知鹤言语柔情,却甚是狠辣,“礼部尚书,凭权乱政,纵子无方,可为陛下试刀之人。”
我挑眉:“一人,怎够杀鸡儆猴,连根拔除才能乱朝臣之智,才能施君王之威,收服文武。”
闻言,他低眉顺眼地笑了笑,张嘴报出一串名字,都是掌实权的官职,和礼部尚书关系匪浅,又写了一张纸。
他还真就毫不手软地一窝端。
“江卿为君王耳目,朕才可耳聪目明啊。”我捏住他的下颚,作势要凑过去亲他。
江知鹤一身的冰雪尽化,我一摸他的腰肢,他就故意软在我的怀里,像一只蛊惑君王的狐狸精。
“陛下……”他叫我,听起来似乎满腔柔情。
我抬眸看他,却总觉得似乎江知鹤并不够真心。
真心与否,听着玄乎,但是真的相处起来,却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无意强逼他,可他如此岿然不动、坚如磐石,实在叫我挫败。
他对我,仍然防备又谨慎,不肯脱下伪装,我看着都替他累。
似乎只有在床上,情到浓时,才能看见他一点点裸露的内里,才能看见那个对我毫无防备的江知鹤。
那个江知鹤被他藏起来了,我要把他找出来。
案牍上的那张纸被我扫在地面,我把江知鹤用力压在桌上,他后背贴着冰冷的桌面,眉间不自觉地蹙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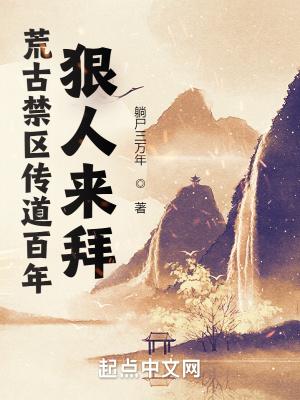
![男主绿得人发慌[穿书]](/img/9971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