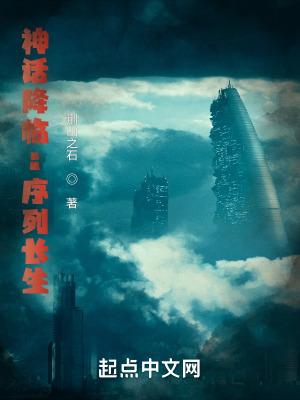车臣小说>奇洛李维斯回信在线阅读 > 第14章(第3页)
第14章(第3页)
陈挽动作顿了下,有点不解,也有一点失落,但他不会厚着脸皮留下来,笑道:“那赵先生慢慢品尝,我先回去休息了,有事随时叫我。”
赵声阁:“……”
谭又明恰好撞在枪口上,打电话过来:“听说你下去喝酒了?”
“伙计,”赵声阁温和地警告他:“我不太希望再在我的房间里看到陌生的活物。”
“……”谭又明大呼喊冤,“不是我!”他跟赵声阁混多少年了,怎么会冒着被他丢进海里喂鲨鱼的风险干这种蠢事。
赵声阁没有听他解释,把电话挂了。
他尝了一口陈挽醒好的酒,帕尔马皇后的香气已经消失了。
次日早上六点,鲸舰17号已经穿过吉西海峡,风光一下开阔起来。
陈挽起得很早,打算欣赏一番大名鼎鼎的纱岛日出。
没想到有人比他更早。
赵声阁就站在甲板上,海风一吹,像个在拍海上杂志的冷酷男模。
陈挽探了下头,又收了回来,因为他觉得现在走过去显得很刻意,不过马上又觉得自己这个动作不太稳重。
赵声阁神通广大,背后长了眼睛,知道有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像个地鼠一样缩了回去。
不过他以为陈挽走了,但陈挽其实就站在船舱的长廊尾上,透过窗户同他看了同一出日出。
陈挽一向很会自我安慰,甚至自娱自乐想到一句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升红日也是一样的,这个共此时是他单方面赋予的,无需得到对方允许,因为他也没有惊扰到对方。
虽然他和赵声阁近在咫尺,其实一直隔着天涯,所以得共此时一刻,陈挽也觉值得庆贺与珍藏。
游轮已经到了海域腹地,受暖流影响,这个月份有大量深海鱼溯迁,谭又明说中午要吃海鲜全宴。
船上可以现捕现杀,这种级别的游轮都有全套捕捞设施,捕鱼证等一系列手续也齐全,客人也可亲自海钓,再交给后厨。
一船少爷昨晚在赌牌上玩得筋疲力尽,个个睡到日上三竿,海钓是不可能了。
后厨天没亮就展开了航钓,虾蟹贝螺深海鱼,战果斐然。
陈挽去捕钓的甲板上看了一眼,虽然上船的时候每位客人都填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病史、过敏源和忌口都很详尽,但还是要跟后厨check一遍才安心,要是在这汪洋大海上出了什么问题,急救都来不及。
跟管家和后厨确认过之后,陈挽乘坐电梯回到三层准备回房间洗个澡换套衣服,甲板上全是活蹦乱跳的海物,他的裤脚湿了,衣服上也沾了很淡的海腥味。
电梯门一开,迎面来了几个人,看到陈挽,打招呼。
陈挽笑着回应,余光检索到了赵声阁,不动声色往左边挪了半分,并把手背到身后,在甲板上的时候,有条数十斤的鳕鱼蹦出来了,他顺手帮船工拿了工具。
赵声阁看到陈挽一出了电梯就不自觉站到秦兆霆身边去,和大家寒暄。
走廊长而窄,擦肩时,陈挽也尽量地往另一边靠,窄道被他隔出公路大道的宽距,尽可能给赵声阁留下最大的同行空间。
非常地礼貌。
赵声阁目不斜视走过去,忽然,他回头,盯了眼那个走远的背影。
沈宗年问:“怎么?”
赵声阁手插在裤兜里,摩挲着卡地亚打火机:“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