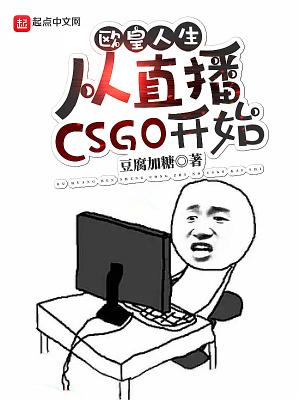车臣小说>不渝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月光从破碎的窗棂洒下,手里的那根紫杉木洁白光滑,带着灰烬的余热,就如同数十分钟之前那个人消失在夜风中的体温。
眼前像是有无数黑暗潮水般的蔓延而来,冰冷的看不见的巨手一直把她拖进深渊里。她抱着魔杖,呆愣愣地跪在原地,任由眼泪一滴滴掉在烧焦的木头上。
不知过了多久,视力暂时恢复了,她仍跪着,浑然不觉指尖已经被余烬烫伤。尽管她知道他不可能被埋在废墟下面,却还是一块一块机械地挖开砖墙与碎木头。
她最终只找到一片被烧的焦黑的长袍碎片,那是他临走时穿的袍子。她才抱过他不久,还没有忘记袍子的面料与上面的纹理。
纳吉尼将它收进了长袍内侧的口袋。
她跪了好久好久,一直到眼泪都流干了。
终于,楼下花园里传出的说话声将纳吉尼扯回现实,傲罗们姗姗来迟。她最后看了一眼婴儿床前面的女尸,伸手轻轻合上她碧绿色的眼睛。
“抱歉。”
纳吉尼站起来,对她鞠了一躬,在来人上来之前幻影移形了。
voldeort消失的第一个星期,食死徒迅速分崩离析。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撇清关系,力求自保,假装自己只是中了夺魂咒。只有贝拉特里克斯、鲁道夫斯、巴蒂等几个年轻人格外忠心,负隅顽抗。他们逃亡的过程中杀死了几个傲罗和不少麻瓜,再加上很久以前的那些旧账,通通被翻出来,记在已经灰飞烟灭的voldeort头上。
纳吉尼枯坐在弗恩堡书房他常坐的雕花大靠背椅上,整整三天不曾合眼,水米未进。
她不止一次地崩溃大哭,哭到干呕。
她狠狠地掐自己,试图从这个恐怖的噩梦里挣脱出来,可是她没有醒来,voldeort也没有回来。
她一次一次转动手上的订婚戒指,念出他过去和现在的名字,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仿佛真的不存在了。
艾比把书房的墙壁都撞掉了皮,也没能劝得动她。
纳吉尼什么也听不进去。像有一把带着尖刺的大锤正在她脑海里一下一下地重击,每一下都是鲜血淋漓的彻骨剧痛,直到把“他死了”这几个词儿嵌进去。起初她不愿意相信,因为voldeort并没有融合所有魂器,她手上就有一个挂坠盒——那是他亲手为她戴在颈上的。可是自从他出事以后,纳吉尼就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了,挂坠盒里的魂片就好像沉睡了一样,静悄悄地,任凭她怎么呼唤或是打开,都毫无动静,她甚至尝试着亲吻那个挂坠盒,就好像亲吻voldeort本人那样,依旧毫无作用。
而后来食死徒的反应和《预言家日报》上白纸黑字的报道证明了一切,voldeort好像真的不在了,他建立的组织和权力中心一夜间分崩离析。
纳吉尼还记得在那座几乎被炸成废墟的房子里疯狂翻找的时候,除了他的魔杖和黑袍碎片,什么都没找到。就仿佛他真的尸骨无存了。
可是他怎么会死呢?他从来都是那么强大……而且他不是说,他早已采取措施防止死亡了么……
第四天纳吉尼终于睡着了,梦里还是个婴儿的“大难不死的男孩”在报纸上露出傻乎乎的微笑,笑着笑着他的脸就变成了几年前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呼吸的蛇脸死胎。他的嘴巴裂开了,仿佛要把纳吉尼吞下去。
于是她尖叫一声,从梦里惊醒了。攥着挂坠盒的手上冷汗淋漓,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没有voldeort温柔的安抚,他再也不会出现,在床边俯下身,似真似假地问她怎么了。纳吉尼又想起她产后抑郁的那两年,即使她赌气不和voldeort睡一张床,后者也曾在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悄悄进来掖好被子,亲吻她的额头。那是他罕见的、不为世人所知的温柔。
这么多年了,他也许缺乏对爱的感知,也许不相信爱,也许骗过她太多次,也许一直在利用她,但他的确给了她想要的婚姻和独宠,给了她想要的一切。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心脏仍一阵一阵的刺痛。
报纸上一条条大写的标题刺入她的眼帘,那些曾经被他握有把柄的记者再也没有了桎梏,开始大肆写他是纵火犯与杀人犯,他带来了恐怖与灾难,他比格林德沃更加邪恶残暴。他所犯的罪行就这样白纸黑字地一条条被呈在眼前,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确杀了很多的人,纳吉尼也亲眼见证了他的罪孽。
即使这般,她好像仍然无法接受他的离去,无法接受要在没有他的地方独自生存下去。血魔咒改变了她的人生,改变了她的性格,但她也因此遇上了他,与他这样的人相识,竟让她觉得一切苦难都是值得的。
人们把她当做黑魔王闲时饲养的金丝雀,毕竟她嫁给了他,跟在他身边,却连钻心咒和杀戮咒也不会用。voldeort其实知道那些说法,他就是这样讳而不言,却小心翼翼地维护了她的天真。他教过她黑魔法,向她展示过他残酷世界的小小一角,但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她变得强大,让她有能力自保,他从来不曾强迫她接触这些。
世人当他是魔鬼,是灾厄,但他却是她的家,她的港湾,她的全部。除了她自己,没人知道,voldeort其实一直都对她很好,他把他仅有的微薄的温柔和宠溺都给了她一个人。
可如今命运把他夺走了。
纳吉尼惊惧地意识到,她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或许还会没有钱,没有住所。离开了voldeort,她什么都不是。
她恐惧于没有他的漫长岁月。
远处传来了巨响,是傲罗在攻击弗恩堡防御阵的结界。纳吉尼站了起来,却因为低血糖差点晕倒。噗的一声,艾比出现在椅子旁边,扶住了她,家养小精灵网球一般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