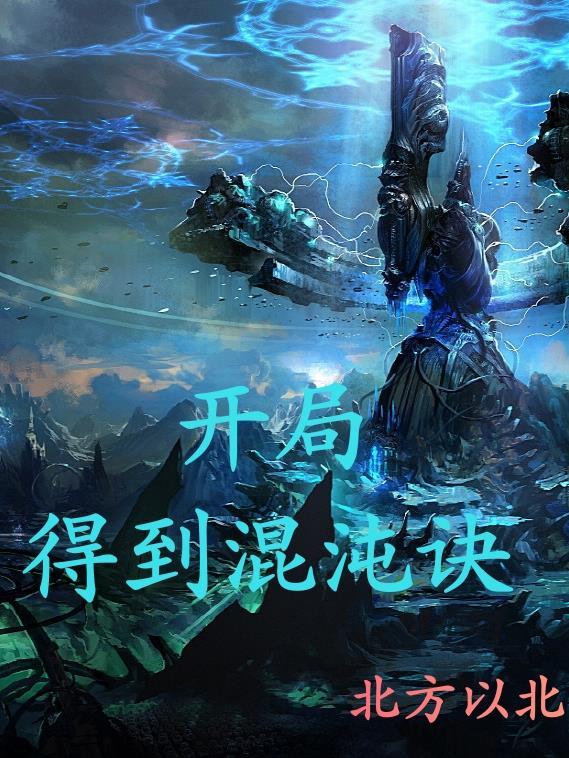车臣小说>落魄山是什么 > 第86章(第1页)
第86章(第1页)
然而白无秋还是没心没肺的同他说笑,完全置身事外般,章景又道:“唐小姐能有这等心胸实属了得,章某在这里先恭喜唐小姐同心上人喜结良缘,只是不知接下来该如何。”
唐素先是愣了愣,随后笑意更深了,捏着帕子就笑:“章公子不妨问问白公子呢。”
章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唐素的笑实在令人费解,但直觉告诉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望向白无秋,果然是蓄谋已久的表情。
章景顿感不妙,忙问:“你要做什么?”
白无秋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道:“还请哥哥委屈委屈,扮演一下我的娘子。”
林中鸟雀四散,惊得许桥惊醒,大概瞥了眼几人所处的位置,无奈的扯起一根细草咀嚼,心中却腹诽白无秋不愧能想出此等法子来。
现在的章景相当于两只脚踏上了贼船,若是让尚叶直接去商量,肯定不行,于是白无秋和白全晨想了这么个法子来。就算章景后悔,也绝逃不出锦城的范围,白无秋就是个疯子,谁知道他是怎么劝说下来白无源的,逼得他爹气到太医馆,当然,这些他都不会和章景提及半分的。
——
七夕前,锦城最大的佳话便是白家和唐家三世交好,金玉良缘,却不想那朝中杀出个探花郎来,几句话就撤回了唐白两家的喜事。有人打听过来才知那人背景雄厚,霎时讥讽的、同情的,各种落井下石接踵而至,几方对家早就恨不得白家消失灭迹,对此更是奚落。
本以为白家至此会抬不起头来,却没想到,不到半月,白家也宣称寻得良缘,据闻那女子是一家普通人户,娘家遥远,不愿意在锦绣城抛头露面,就商议着只请了极少一部分人参加婚宴,其中就有唐素和探花郎。
那日白家府外聚众乌泱泱一片,有人说白无秋是赌气随便找了个人来抵抗探花郎的行为,也有人说那女子定比唐素貌美,不然怎么能入得了白家挑剔的眼。
然则实际不是,白家一片张灯结彩,气派喜庆之景,请来的宾客也不乏尊贵身份的,新郎官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过,朋友拉着喝酒也不拒,尤其居然和那探花郎情头手足兄弟,相谈甚欢,全然卡不出一点间隙。
奇了怪了,这两人为何这么快冰释前嫌,一丝尴尬都没有,搞得唐素娘家脸上有些挂不住彩,唐素却格外开朗,早早去找新娘了。
章景不安坐在床沿,外头的喧嚣仿佛和自己没关系,自动隔绝了一道屏障。有了唐素,才敢松懈下半分来,说实话,章景的个头并不矮,和白无秋站在一起,还显得白无秋灵巧一些。
于是众人看到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只见那新娘体格格外雄厚,几乎和白无秋差不多了,走路起来也十分别扭,一看就不是大家闺秀出来的。众人疑虑却不敢多嘴,白无源和白大公子都在,谁也不敢唱反调,都乐呵呵祝贺。
章景内心忐忑极了,头上的朱钗和盖头使得头上沉沉,勉强能看到脚下的路,周围的人声几乎要把人淹没,章景知道,那些人一定没有多少真心,白无秋说不定早就成为笑柄了。
紧张之际,那双纤长的冰手握了上来,章景心神定住,对方的温度传来,凉丝丝的,缓解了不少焦躁,章景深深提了口气,回握过去。因为他知道,白无秋一定需要自己的回应,两人顺理成章拜完堂,走完了所有过程。
深夜,帐中灯摇,白无秋被灌得有些醉,心中无比雀跃,踏进洞房时候脚下都是虚浮的,踩着云朵一样飘飘然,眼神很快锁定到床边的人身上。
章景等候多时,没有人打扰就擅自将盖头揭了下来,躺在床头看书,见着一身酒味的白无秋,眉头不由得一皱:“你怎么喝成这样。”
话音刚落,白无秋就扑了上来,哼哼唧唧朝章景颈窝钻:“哥哥把盖头盖上嘛。”
章景不解:“我又不是女子,盖不盖都无所谓吧。”
白无秋一听不乐意了,义正言辞道:“盖头只有新郎官才能揭,哥哥这都不知道。”说着就把盖头住起来给章景盖上。
章景被这一番话弄得不知如何反驳,脸颊绯红,让原本抹了胭脂的他更加诱人,今日感受,的确前所未闻,他竟也变得敏感了许多,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白无秋心满意足挑起盖头细细打量,扑面而来是章景那张羞涩还未褪去的摸样,章景的长相浓眉大眼,唐素特意按照章景的面部特点施粉,面上只做了简单的提白,眼尾用了桃红,拉出一条细长的线,对上那对剑眉和薄唇,妖冶中带着纯真。
盯得时间长了,章景有些不自在,把头别到另一边,白无秋才傻乎乎把章景圈进怀中,揉着章景的手唤道:“娘子,我们终于修成正果了。”
“闭嘴,再敢这么叫我就滚出去。”章景激得起了层鸡皮疙瘩,实在想不出人前醉玉颓山、金质玉相的人是这么个德行。
白无秋仗着自己喝了酒,蛮不讲理,就埋在章景的胸前,胡言乱语:“哥哥既然与我成亲,就该是夫妻,哥哥也该唤我为相公,行夫妻之事。”
“我看你是喝醉了,早些歇息吧。”章景把人从身上扯下来,白无秋双眼迷离,趁章景不注意时,嘴巴就啄了上去。
两唇缠绵悱恻,章景一时情动,双手顺势勾上白无秋脖颈,嫣红的唇色留下一串红印,白无秋把床纱放下,烛台微亮,照起一室春光。
——
又一年,荒州北台新上任了一位县令,熟悉的人却知道,那是故人归来,是来重治荒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