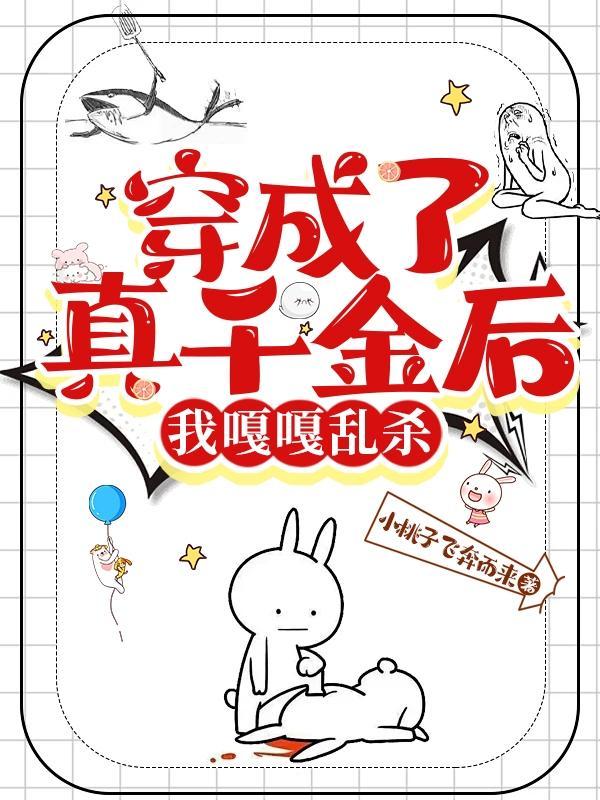车臣小说>寒舟渡燕识衣免费阅读 > 第39节(第2页)
第39节(第2页)
不知从何处吹来一丝凉飕飕的风,沈妙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这人原来竟是个疯子!
倘若和他坦陈自己的身份,他会不会恼羞成怒直接将自己杀了灭口?
正思量着如何应对,忽听见衣料窸窣作响,似是陈令延站了起来,“我已给卫凛送了信,你便老实等在此处,不要妄想逃跑,我会派人看着你。”
也不待她作何回答,陈令延脚步声响,已经推门而出。
随即传来几声铁索碰撞的响动,想来是给屋门上了锁。
屋内又恢复一片死寂,静得只能听见她自己的呼吸声。
额角的伤处一阵阵发疼,身上似乎也发起了热,脑中昏昏沉沉,沈妙舟强迫着自己打起精神,要尽早想法子脱身,总不能这般任人鱼肉。
陈家小贼既然蒙住了她的眼睛,说明如非必要,他还不想杀她。
勉强算是一桩好事罢。
当务之急是要解开腕上的绳索,这样才能有起码的还手之力。
沈妙舟费力地转过身,借着墙壁摩擦,一点一点蹭高蒙在眼前的布料。
终于能看见周遭的环境,她发现自己是被关在了一间寻常的小屋里,从木窗向外看去,屋外天色已经黑透,像是到了深夜。
好在桌案上点了一盏灯,光线虽弱,却也能照亮四周的环境。
此处只有一张床和简单几样桌椅摆设,但收拾得很是整洁,光线下也不见什么灰尘,布局构造看起来倒是有点像普通人家的客房。
只是她四处寻遍,也找不到任何尖锐之物,只能尝试用桌角慢慢磨断绳索,然而她一直磨到双臂酸软,腕间渗出血来,也只是将绳子稍稍磨损了一层。
说不沮丧是假的。
她觉得自己都要委屈死了!
但是没办法,沮丧没有用,只能振作精神,想办法自救。
沈妙舟歇息一阵,感觉身上又蓄了一些力气,便要继续磨割绳索,突然之间,想到桌案上的那支烛火,心头一喜,当即站起身来,用牙齿叼下灯罩,背对着烛火,去燎腕间的绳索。
她看不见火苗的位置,只能咬牙忍着被火灼伤的痛意,烧一会停一会,直到疼出满头豆大的汗珠,终于烧断了腕间的麻绳。
沈妙舟长舒一口气。
虽然燎断了绳子,但她伤寒本就未好,此刻又发起高热来,头脑更加昏沉,根本没有体力支撑她逃出去,只能先养足力气,再见机行事。
她把烧断的绳子按自己能挣脱的法子重新系成结,放在身侧,又将蒙眼布再次拉下来,一切布置妥当后,再也耐不住疲累,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夜间她睡睡醒醒,心里总不踏实,迷迷糊糊挨到第二日清晨,门上忽然传来几声响动,像是有人要开锁进来。
她立即惊醒过来,迅速地将双手反背到身后,套上事先打好结的绳索,假作仍未睡醒的样子。
很快有人推开屋门,走了进来。
她嗅到一阵饭菜的香气。
原来是给她送饭。
来人将饭菜放到她面前,唤道:“醒醒,吃饭了。”
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并非陈令延。
送饭的人并未过多停留,放下饭便退了出去,又将屋门锁好。
沈妙舟用过饭,精神好了几分,躺在床上暗暗盘算如何脱身。
如今她体力不济,又不知对方虚实,实在难以对付,在脑中想了数条计策,却又纷纷否掉,不觉间一日过去,天色渐晚,门外又传来开锁的声音。
沈妙舟心里忽然有种极不祥的预感,紧张地坐起身来。
呀的一声,门板被推开,走进来一人。
来人一步一步,慢慢踱到她身前。
沈妙舟的心陡然悬起,砰砰急跳。
在落针可闻的寂静中,来人打量了她半晌,忽然嗤了一声:“我原以为他待你有所不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果然是陈令延。
沈妙舟紧张地吞咽了一下。
陈令延冷笑了一声,继续道:“消息送了去,他竟连问都不问一声,果然还是那个冷心冷情的怪物。”
所以,是卫凛不肯答应他的条件来换她回去?
说不出缘由,但沈妙舟隐隐不大相信。
她只觉得卫凛不会全然不顾她的生死。就算陈令延开出的条件他难以答允,应当也不会直接置之不理,或许他被皇帝关起来下了狱,根本就收不到信。
似乎是看出了她的怀疑,陈令延讥讽道:“难不成到此时,你还对他心存幻想?卫凛昨日的确是受了些责罚,但一没下狱,二没圈禁,他神智可清醒得很。”
“我不但派人给卫凛送了消息,还给你那个婢女留了信,就算我的人送信出了差池,你那婢女总会想尽办法告知他罢?可是我等了整整一日一夜,呵,卫府甚至连一个暗卫都没有调动。”
沈妙舟微微一愣。
卫凛真的会全然对她不闻不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