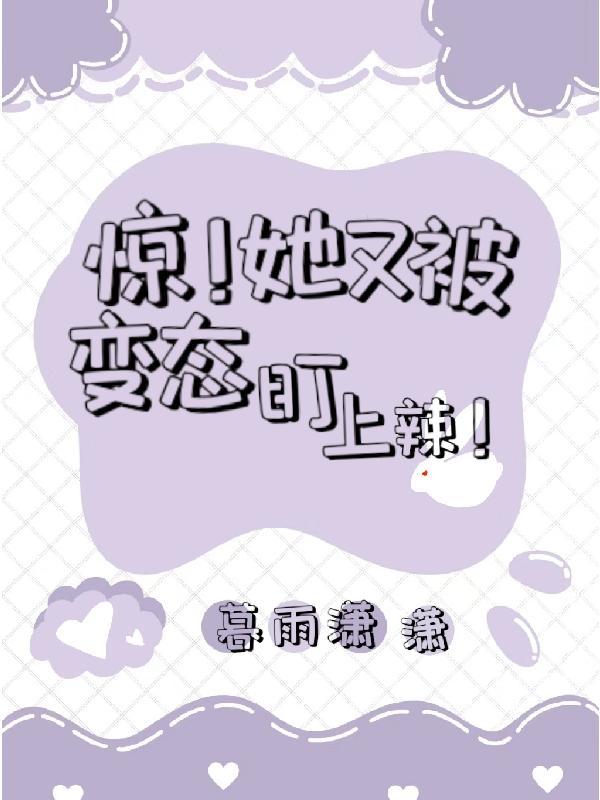车臣小说>本宫贤良淑德巫明丽 > 第五十二章 登门送礼(第2页)
第五十二章 登门送礼(第2页)
陈太太心中狂喜,却故作不知,忙笑道:“既然是于大人的爱徒,那就是一家人,既然来了,何妨请进门喝两杯酒,也是待客的道理。”
于老太太十分犹豫,其他人想看热闹,也跟着说如此应当:“陈太太说的对,那别人受人之托送个寿礼来,怎么着也要招待人家一顿饭,不然叫人白跑这一趟呢?也是给您添个喜的意思。”
于老太太勉强说道:“只看我儿的意思罢了。”
一时于青夫妻回来了,领着六个人回来,打头一个俊俏公子,衣裘带玉的,清俊贵气极了,又有一个白面无须的男人,手里捧着一个匣子,胖胖的,面带笑容,但不说话,又有一个拥着大红锦缎面子灰鼠皮里子斗篷、手里抱着大红包袱的中年女子,说不清美丑妍媸,只觉得她严肃威风,眼睛看人像甩刀似的。
他们后面还有三个人,都是仆从打扮,抬的抬,抱的抱,跟着进到了院子里。
于青与那小公子引荐:“薛公子,这是家母。”
来人正是薛芹,早出门时,他和王喜哥、珍珠聊了聊,确信于家一家子在皇子夫妻那里颇有体面,于是不等于青再介绍他,他就先笑嘻嘻地与于老太太叉手行礼,道:“问老太太安。家父龙游将军,和于大人算半个同僚,今儿接我一个上峰的请托,向您老祝寿来了!我家姓薛,我行四,他们都叫我小四儿。”
于老太太忙道:“薛公子无须多礼,您有心上这儿来,我们家贫,接待没个礼数,您见笑了。”
不知道又是哪个傻子,直挺挺地说道:“哪家的徒弟这么没眼色,师父做寿,自己不来,倒派个人来,这派头,真是上了天了。”
陈太太还没说话,有另一个人把那人捂着嘴拖下去了。
薛芹也不计较,就问:“老太太,那我讨杯酒喝?”
于老太太私心也希望儿子能有个更好的依靠,于是亲自安排下薛芹带来的人,薛芹自然是坐主桌,三个仆从坐在另一张桌上,但是王喜哥和珍珠,薛芹就犯了难了,他连他俩能不能在这吃饭都不知道。
见状王喜哥还是没说话,倒是珍珠说了:“我和王兄弟就不吃了,送完了寿礼,得赶紧回去复命呢。”说罢,又低声与于青说道,“来往多了,反而不便,请您谅解。”
于青拱手,道:“敢问嫂子大名?嫂子高义,请恕我这里便招待不周了。”
珍珠笑笑:“我省得的。”
说完,珍珠示意薛芹交上礼单,老太太老眼昏花了,她的孙女儿帮着看了一通,薛芹就夸:“这么小的姑娘,认得这么多字儿,真不错,比我还能干。”
小姑娘被夸得脸红红的,往后一躲,陈太太一看,怎么于家小姑娘往后躲就躲到了自家儿子旁边,她的宝贝儿子还低着头和那小丫头有说有笑?
不过陈太太倒也顾不上想儿子了,她将寿礼单子核了一遍,确信是皇子殿下送来的无疑。
众人惊讶间——这笔寿礼可足够一个小户人家一年的嚼用了——薛芹和三个仆从将细布、油布等物搬了下来,交与于青媳妇拿去收着。
王喜哥递上匣子,里面是官造点心七十二件,件件精致可爱,过糖过油,还洒了金箔。
珍珠递了包袱,里面都是崭新的零碎物件,她说道:“这是我们家主母的意思,听说于师父儿女年纪渐渐上来,要学书啦、当差啦、见客啦,没个门面就不大好,于是将时兴的缎子片儿包了来。好请老太太知道,原不是用剩下的,因为要送去刺绣、加缀珠玉,于是都先裁开来粗缝上,要做时再拆了缝线仔细缝了。”
说罢,珍珠打开包袱给于青媳妇看了一眼,里面放着五颜六色四套衣料,梅红桃红绛红的都有,顶上一件恰露出半朵绣花,是苏工绣蝴蝶赶花样儿。
陈太太道:“是好东西,颜色也好,鲜亮的鲜亮,沉稳的沉稳,既有老太太的,也有小姑娘的,送到坎儿上了。”
珍珠将包袱重新扎好,交给了于青媳妇。
珍珠代巫明丽喝了杯酒,与王喜哥一同告辞,有之前薛芹雇的那辆车送他们回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