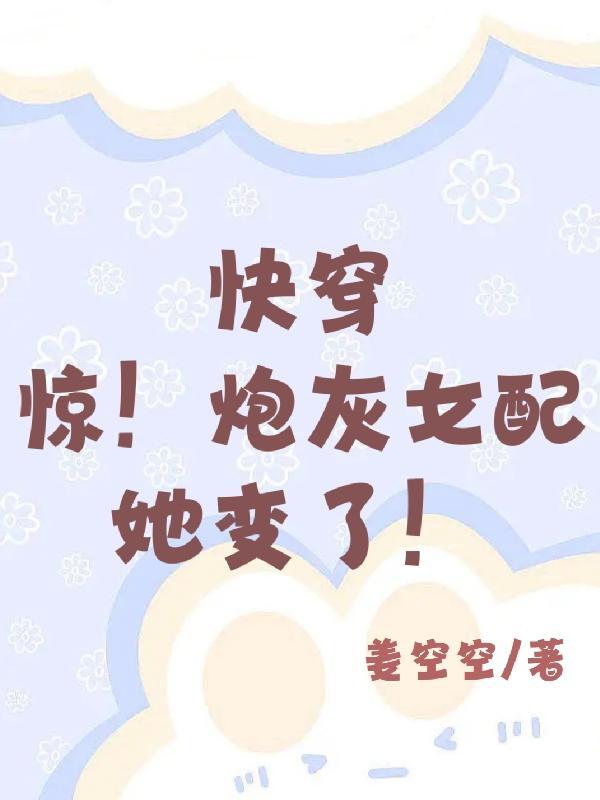车臣小说>乌兰巴托的夜知乎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好心人”
陈东实正看着电视,门“呼”地一声被推开。陈素茹领着陈斌双双走了进来。
几天不见,陈斌那小子清瘦不少。想起上次见面还是在劳务市场,也不知道他工作落实了没有,陈东实又犯起了替别人操心的烂毛病。
“喊人。”陈素茹推了陈斌一把,男孩方涩涩唤道:“陈叔叔好。”
“你们怎么来了”陈东实虽不喜陈斌,但好在他妈妈还算会做人,能主动探望已属难得,他向来是别人给自己一分,他要还十分的人。
陈素茹擦了擦手,说:“我是向上回在少管所遇到的那个小妮子打听的,她说你最近遇了事,住了院,吓得我赶紧带孩子过来看一眼。好心人我该怎么称呼你?斌儿说你是他朋友,我想总不好直呼你大名。”
“叫我老陈就好。”陈东实客气地笑了笑,抬眼看向旁边的陈斌,“怎么样,工作落实好了吗?你说要自己找,成果怎么样了?”
“找好了找好了,”陈素茹忙替男孩答,“帮我一个老主顾,在他店里做事,擦盘子。”
“也好,”陈东实满是欣慰地摸了摸男孩的头,“靠双手赚钱,不寒碜。你叔我像你这么大,也擦过盘子,算不得丢脸。”
此话不假,陈东实进社会早,服务员、仓储、保安、货工、泥瓦匠凡是能赚钱的,对学历要求不高的,他几乎都做过。这也练就他一身的慈心,因为见过太多的苦,很多时候并不单是他想帮,而是良心告诉他不得不帮。
对陈家母子,也是如此。
陈东实从给童童的那一沓钱里抽出一两张,塞到陈斌手上,“长身体的时候,想吃啥自己买点,别苦了自己。”
“这怎么好意思”陈素茹赶忙将钱推了回去,赔笑道:“说好的是我们来看你,怎么好意思让你掏钱?”
说罢从皱巴巴的钱包里拿出一封红包,递到陈东实手上。
“我没什么本事,这都是我这些天辛辛苦苦攒下的,您别嫌脏”
陈素茹说着说着,神色又伤感起来。陈东实捏着那红包,如千斤压顶,诚惶诚恐。
他深知,女人口中的“攒”,无非又是开张接客,乌兰巴托色情业发达,像陈素茹这样的女人数不胜数,扫黄打非这么多年,这行当非但没有落寞,反而日益昌盛。
“你看看,你妈多不容易。”陈东实看了陈斌一眼,知道他不爱听,但还是多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学会帮你妈多分担分担。做错事不要紧,只要别一错再错,再让你妈担心就好。”
“嗯。”陈斌难得有了些反应,他向来反骨难驯,得到他的表态难如登天。
“对了,我进来时,看到有个女的一直站在门口,慌兮兮的,不知道在干什么。”陈素茹像是想起了什么,“她身边还带着孩子,比斌儿小一点,也是个男孩。”
陈东实瞟了眼门口,没猜错的话,门外守着的应该是老钟老婆和小钟。
陈家母子坐了一会便走了,临走前洗了好些个水果放在床头。陈东实让陈斌出去时把外头两人叫进来,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一定是为钟国华求情来了。
“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该的,可是大兄弟,我一个妇女家,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呀”老钟媳妇进门便是一通哭嚎,差点就要给陈东实跪下,“老钟现在就在局子里,警察二十四小时看着。你说这要咱娘两怎么办?这个家不能没有他呀”
陈东实听得心里一阵酸楚。短短数日,大钟和老钟就接一连二出了事,虽说是他们自作孽,可归根源头,还是那封举报信惹出的事。后续一连串因果皆因自己而起,陈东实不得不背负着一份负罪感。
可是,刀子是实实在在捅在自己身上的,他又何尝不心灰?昔日的施恩者对自己拔刀相向,相比生理上的疼痛,陈东实更后怕那转瞬即变的人心。
“这事我做不了主”陈东实躲开老钟媳妇那双泪汪汪的眼,强忍住挣扎:“就算我出面谅解,也抹不去他蓄意伤人的事实。警察那边,该怎么判还得要怎么判。”
“不会的”女人抹了把泪,支撑着从地上站起,“老二说你同那帮警察熟,您大人有大量,高抬贵手,放过老钟一马吧”
陈东实看了眼旁边的小钟,从进来到现在,他一字未发,还是像从前那样温和平静,有着他那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成熟与淡定。
小钟将母亲扶住,细声安慰道:“这事本就是我爸做错了,你又何必让陈叔难做人”
“你个没良心的,他是你亲爸!”老钟媳妇瞬间垮了脸,“养不熟的白眼狼,你忘了你哥是怎么进去的?”
陈东实心下一紧,乍地想起了什么,问:“对了,我还纳闷呢,老钟怎么知道是我举报的大钟,难不成”
他将怀疑的目光瞥向钟健飞。
“不是我,”小钟忙摇了摇头,“我没说。谁都没说。”
“那是谁说的?”
陈东实抓起他的手,厉声质问。
“一个跛子,男的。”钟健飞往后扯了扯,没扯开,索性坦白,“好像是姓梁。”
梁泽
陈东实如坠冰窟,通体的冷意从骨血深处向外爆裂,直接瘫倒在了床畔。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梁泽在告诉老钟这些时,当真一点都没考虑过自己的感受吗?
陈东实强撑着床把手站起,踉跄两步,又失魂落魄地坐回到床头,思绪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