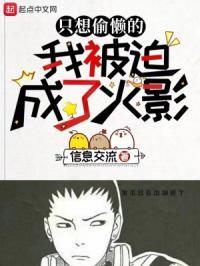车臣小说>红糖鸡蛋红枣汤的功效与作用 > 第 2 章你能不能帮我修房子 (第3页)
第 2 章你能不能帮我修房子 (第3页)
撇断。
一根都没放过。
拔干净了,梁白玉抖抖衣裤,抬脚迈出树林,他走了一段路,捡起地上不知谁家掉落的几根山芋藤。
随后沿着这个方向走,来到一块地前。
这家人挖了三分之一的地,土都翻在外头,一些碎小藤叶乱糟糟的丢在旁边。
有个土粑里带点红,梁白玉的眼睛一亮,眉间的妖艳褪去不少,涌出几分天真的孩子气。
这一激动,唇色就白了。
梁白玉跳到地里,凑近那个土粑,他蹲下来,颤抖着咬住左手腕的膏药贴,用右手扒开土。
一个小山芋露出了身子,头上有一个黑乎乎的虫洞,它育不良,没被这块地的主人现。也有可能是现了,觉得它太小,还有洞,就懒得要,拔出来又随便丢掉,被土盖了起来。
梁白玉单手挖出山芋,吹掉上面的土。
有一串脚步声从路前方传来,梁白玉抬头眯眼,他还没看清来人的相貌,就认出那宽如山河的肩膀。
男人从梁白玉边上的田埂路过,没有停留。
梁白玉蹲在地里,视线落在男人糙长结实的双手上面,又移向他袖口的红袖章,忽地开口“大叔。”
很普通的称呼,只不过混入了个人特色,尾音入骨的酥,和这个保守淳朴的村子格格不入。
“诶。”梁白玉从地里爬上来,皮鞋上都是泥,他也不在意,潇洒自然的走过去,黑睫下流光闪耀,“你好啊,我叫梁白玉。”
男人沉默。
梁白玉笑吟吟的看着他。
“陈砜。”面前比他高很多的男人这么回答,嗓音不太好听,又哑又浑。
梁白玉近距离看他,现他的年纪还够不上“叔”字。
当事人却没纠正。
“你会修房子吗土房。”梁白玉刚才咬过膏药贴,唇齿间有一点药味,不难闻,他的眼型不知遗传了父亲还是母亲,往下看并没有任何压迫感,只有很多虔诚的情。
而当他长时间仰视一个人的时候,会让被他注视的人产生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仿佛在被他全心全意的依赖,依恋。
就像现在。
被他仰视的人抿住干裂唇角,低下头,检查起了挂在身侧的军用水壶。
“不会啊”梁白玉擦着手上的泥土,眼角眉梢都是让人心软的哀愁,他很轻的叹了一口气,转头离开。
远处田里有村民在犁田,家里孩子兴高采烈的跟在后面,扒拉泥巴找小洞,捉泥鳅。
孩子欢呼的大叫声没飘过来。
走在田埂上的年轻人自成一方天地,像一副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风里夹着细小雨点,画浸了水,快要烂掉了。
“会。”
后面倏然响起声音,梁白玉纤瘦的身形一顿,他回头时已是满脸不敢置信的笑意,“真的啊”
陈砜“嗯”了声,他的双眼很有神,左耳的阻隔扣上落了小雨点。
“那你能不能帮我修房子”
梁白玉的手伸向男人,指尖触到他的迷彩服,手指捏住他精壮的胳膊,慢慢往下,力道并不重,小羽毛似的。
男人眉头打结,要躲。
梁白玉已经撤回手,他垂眼,轻轻吹掉指间的小针叶,眼皮一抬,笑意惑人“我付你工钱啊。”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