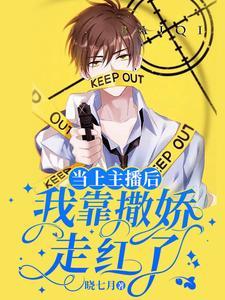车臣小说>让我死在你怀里笔趣阁 > 远客三(第2页)
远客三(第2页)
唐棠说:“你忘记了?你的拜师大典还没办呢,我好不容易拖着你做完任务,你连拜师大典都不让我参加?”
牧行之一愣。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连牧行之自己都忘了还有拜师大典这件事——他通过了试炼,唐家人已经全然把他当做大师兄来看待了,这个拜师大典,便是对外宣告他的身份,自然不会让他来操心。
关芝芝垂着眼,对他们的谈论充耳不闻,她给唐棠画好了花钿:“好了,看看,就是这样吗?”
唐棠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转过身来,对牧行之说:“云谷主请我去药王谷,但我想云姐姐不会同意的……再说,白化病要是这么轻易就能治,也不会困扰唐家几千年了。”
唐棠知道牧行之大约是真的希望她能去药王谷治病,但或许整个唐家,也只有牧行之一个人觉得她去药王谷真的是去治病的。
“可是……”
唐棠将手指放在膝上,静静地看着他:“你想我去么?”
“当然。为什么不去?”牧行之说。
唐棠仰头看着他,发现他已经换了一身白鹤金松的纹袍——唐家的弟子袍有严格的规制,像关芝芝这样入了唐家但不能
算唐家人的,只能同侍童们一般穿无纹白袍,唐年那样的支脉是青云松纹,嫡脉与主脉虽然都是白鹤金松,却也有细微的不同。
换上这身衣袍,他已是唐家人承认的唐家主脉,唐家大师兄了。
可牧行之还是没法理解唐棠为什么拒绝去药王谷治病,就像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并不姓唐的唐家新晋大师兄不能理解唐家一样。
他可以是唐家的大师兄,是唐家的座上宾,资源、声名、脸面。要什么唐家都可以给他。但在唐家,他终究是格格不入的远客。
“血脉”、“世家”,有些东西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事情,虚无缥缈,却又坚韧不拔,没有丝毫道理可言。
唐棠耸了耸肩,说:“因为我不想去药王谷。”
他以为她能去吗?就算能去,唐棠也不想去。治病要这么多年,她走了谁来盯着她的男主?就说这次历练任务,她要是不跟着牧行之,这傻狗子早死地底下了。
还是那句话,唐棠只想做任务,老老实实把任务做完走人,不要节外生枝。
但她不知道,牧行之把她的话理解为“害怕”。
唐棠从没有离开过唐家,即使偷跑下山,也只是一两天的事情,如果要去药王谷治病,一年两年都打不住,唐家人把她保护得很严,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是新奇的,却也是令人不安的。
他又想起今日云中任找上映棠阁时,在外面对他说的话,云中任看起来是
真的很对唐棠的病感兴趣,很希望她能去药王谷,方便他研究。
唐棠的病是一定要治的,无论是什么原因,他总是要搞清楚的。他想,如果唐家不同意——
拜师大典上人来人往,唐家人都会忙起来,没有人会注意到少了谁。
他又看向唐棠,少女一手捧着脸,正跟关芝芝聊着人间流行的新花色,她对那些人间的事情很感兴趣,分明是修真界世家的大小姐,却和凡人没有区别。
——她不能修炼,早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凡人。
在这修真界,她就像是一个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的远客,遥遥地望着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身影,保持着与她的年龄毫不相符的淡然。
可她会不会有不甘心的时候呢?牧行之兀地想起在藏书阁时,她一手合上剑谱,仰头望着那扇小小的窗外面的天光。她的表情淡淡地,好像含着某种怅然,又好像只是冷眼旁观。
她说:“世上既然有人与天地同寿,就有人命如蜉蝣。”
他们与天地同寿,而她命如蜉蝣。
她自认自己是蜉蝣,牧行之却不这样认为。
谁会眼睁睁地看月亮坠落?
——至少牧行之绝不会。
她的确是跟修真界格格不入的,牧行之从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偶尔也想,是否生命就如同火焰,长短也与热度挂钩?
那些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修真者都是默然的,好像与天地同寿的代价就是化为永恒却沉默的山川河流。
只
有唐棠这一只蜉蝣热烈得令人心惊,就像她雪白额间的剑纹,凌厉的、鲜红的,仿佛往下淌的一抹血,叫人眼热。
他想她做永不熄灭的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