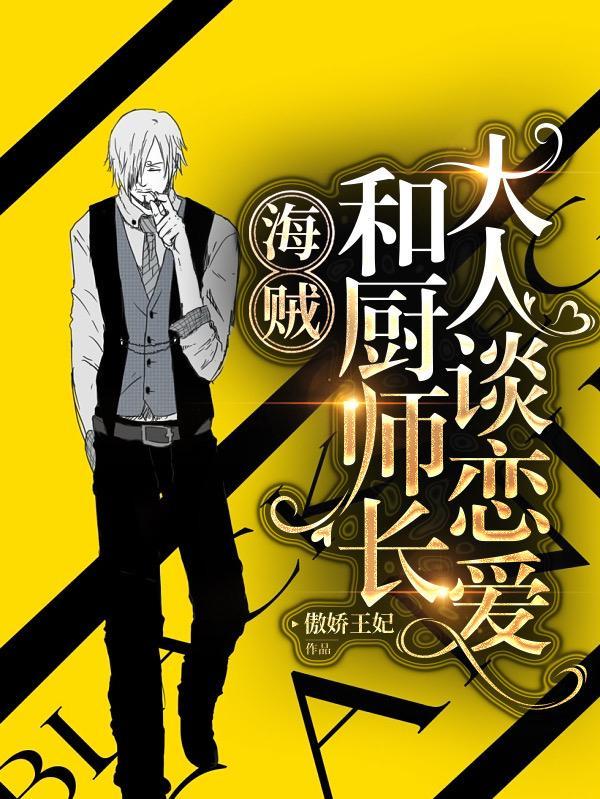车臣小说>一剑江湖手游官网 > 第87章 东院有佳人(第2页)
第87章 东院有佳人(第2页)
趁着袁北庭二人正兴起,欣赏着眼前的字画,此时那亭中已是琴弦拨动,琴声悦起,东院儿的大门也是朝着往来宾客敞开,不少原先在外挑选字画的世家人物皆是醒步摇扇来到院中,其中多少人是奔着字画而来,多少人又是奔着琴声而来就不得而知了。
而袁北庭对这字画本就不感兴趣,能跟着来这东院儿,也只是想瞧瞧这央儿姑娘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让身份高不可攀的世子梁安如此上心。
就如此前掌柜的所说,这央儿的琴技倒真是没得说,“亭上调玉琴,一弦一清心。冷冷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袁北庭听着亭中琴声,不由得有感而,倒是惹得张怀钰有些刮目相看,袁北庭瞧着,不禁有些得意:“本世子,可不仅仅只会使剑!”
张怀钰捂嘴轻笑一声,说道:“那你倒是说说,这央儿姑娘的琴声有何特别之处?”
袁北庭咧嘴一笑,回声道:“这你倒还真考不倒本世子,古琴重音色之变化,每曲子之间的手法和弹奏方式都是大有不同,弹奏古琴者多善泛音,能使人一种空灵飘逸之感,除此之外,这古琴余音绵长不绝,亦如那《广陵散》,多是给人以雷霆般震动之感。”
张怀钰见袁北庭说得如此头头是道,便接着问道:“那你再说说,这央儿姑娘弹得是何种曲子?”
袁北庭听着,知道这小妮子在给自己出难题,哈哈一笑,说道:“这我倒是真说不出来了,不过听着曲调,约莫是江南小调不成?”
张怀钰瞧见眼前之人终是吃瘪,也不再藏着掖着,开口说道:“胭脂榜前三甲中曾评有一美人儿,唤作陈沐芙,说她有闭月羞花之色,除此之外,这陈沐芙如今虽是家道中落,远不及此前那辉煌家世,可她一手琴技当是大家风范,自研的《江南调》更是风靡大江南北,这央儿姑娘如今所弹奏,便是那陈沐芙所作。”
袁北庭听着,恍然大悟,对于这些个文雅风趣之事他是真不太懂,此前那般评言也不过是从二姐那里借用的几句,加上母亲喜欢听琴,他也算是略知一二,再要深入,那他可就是一窍不通了。
袁北庭越过眼前字画,眼中一道微光闪过,那影罩的薄纱便似不复存在一般,袁北庭目光直接掠过一层层阻碍,看向那拨弄琴弦的纤纤玉手,手法熟练,一看就是经过长久练习才能换来此番结果。
“我刚刚看了看那姑娘弹奏的手法,虽是熟练非常,可这无论是揉弦还是勾弦的技艺都不是大家风范,也不是从小练就的底子,这说明,这央儿姑娘的琴乃是后来所学,说不定,也就是那梁安为了能让这央儿姑娘自给自足才安排其学了这门手艺,随后又将其引荐入了千文堂,他这般耗费苦心,说明这央儿姑娘于他而言,倒真是意义非凡呐。”
袁北庭收回此前那般如矩的目光,朝着张怀钰说道,本来一个瞧不见的琴师万不可能值得他这般上心,可一听掌柜的所说这琴师与世子梁安有关,倒是让他来了兴趣,如今一瞧,这其中端倪更是大有说法,袁北庭更是觉得此番来得值当。
不过他也不是上赶着四处去问的主,知道这央儿姑娘身份不一般便好,若是让他拿着这女子身份以此来威胁梁安,一个他是做不出,二个,凭借他的身份,也实在没这个必要。
几曲散过,这东院儿鉴赏字画已是到了散场之际,其中多少世家瞧得上,便直接交由千文堂伙计包起来就好,若是遇上个同样看起眼的,那几人之间便自行组个小竞拍会,价高者得,这东院由于多是些名贵珍品,这般动作也算不得少见,几十幅字画如今已是卖了大半有余,可别小看这二十几幅字画,这每一幅可都是价值千金,这二十几幅,可想而知价值有多高,就这短短几曲,这千文堂已是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曲终人散,待到那些世家人物散去,袁北庭二人也是准备出了东院儿,出千文堂回九重院儿去,此时的央儿在撑船之人的搀扶下上了长廊,同样奔着院儿外而去,她的营生便是弹琴,如今几曲已闭,她自是不会再做过多停留。
小姑娘拄着竹杖在身后,袁北庭回身望去,想瞧得真切一些,却不想这央儿倒是警觉,袁北庭目光望向她的那一刻,央儿已是同样抬眼望来,不过瞧着其无神地双目,便知道,她是真瞧不见了。
“不知二位听着还算满意?”央儿目光掠过二人,便再次回过头看着前方,缓步地踱着,尽管看不见,可这般动作已是成了自然。
袁北庭瞧着央儿脸上不似他人那般不幸之人的那般阴沉,反倒是有着一副比之常人更加的淡然之色,嘴角还时不时得勾起一抹浅笑,显然此女子的心境已是到了常人所不能及之地,听见其问起,袁北庭也是赶忙回声道:“姑娘琴技了得,在下佩服,想必姑娘在这弹奏上是下了大功夫吧?”
央儿听着,淡然一笑,说道:“公子应当是听出了央儿并非是从小练琴的手法?不瞒公子,这弹琴央儿也是近几年才学有所成,还是在他人所助之下,这琴技与那些个世家小姐相比实在是差距甚大,还请公子见谅。”
袁北庭听着,则是摆了摆手,回声道:“倒是姑娘有些妄自菲薄了,弹琴,手法什么的都是其次,姑娘琴声中那股跌宕起伏的真情实感,才是琴声之根本,比起那些只知道作秀摆谱的世家小姐,姑娘的琴声,称得上仙乐。”
央儿听着欢喜,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公子倒是个会讨人欢喜的人物,日后若是公子想听琴了,便来这千文堂,央儿弹给公子听便是,也算是不枉公子这一声夸赞。”
袁北庭哈哈大笑,应了一声算是答应,随后便看着央儿拄着竹杖缓缓离去。
“这女子,不简单呐,如此心境,即使是如我只怕也难以做到。”袁北庭看着那缓缓离去的一袭红衣,感叹道,张怀钰在一旁也是轻叹了一声,说道:“是啊,看着她无神的双目,便知道其是从小便失了光,实在不敢想象这一路走来她究竟吃了多少苦楚,这般独来独往,想来这家里对其也不是放在心上,倒是还不如那世子梁安对她来得亲切。”
二人这般感叹,渐渐地便出了东院,拿着早已包好地二姐的画,二人出了千文堂,奔着九重院儿的方向而去,却不想将将走过几步,却是一人来到二人身前,看腰牌,是烟雨阁的人。
“二位,贺州王邀二位烟雨阁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