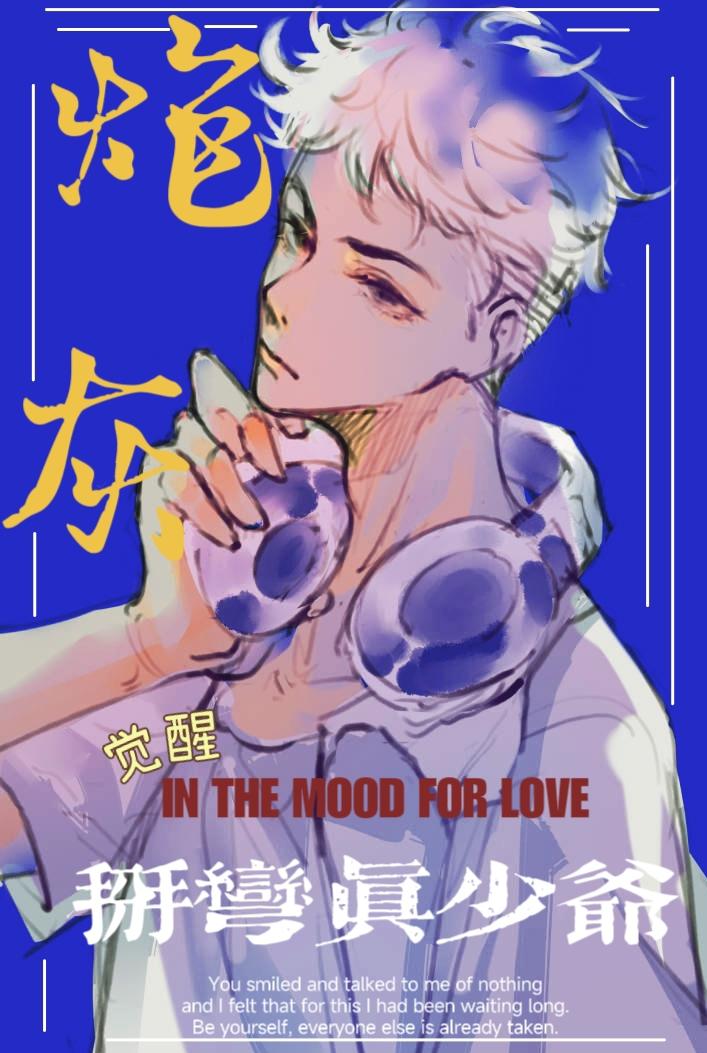车臣小说>摄政王只想篡位晋江 > 第96节(第1页)
第96节(第1页)
他叹息时,眉心微微蹙起,双眼也盛满了欲语还休的悲伤,好似真的很是遗憾。
江怀允深知眼前这人在神态拿捏上最是得心应手,可对上他的漆黑深邃的瞳眸,着实有些狠不下心。
他认真反驳:“我在宫里那段时日,曾与你通过信。”
“阿云是说那两封为免旁人察觉,字字机锋艰涩难懂的传信吗?”谢祁怅然着又叹一声。
江怀允:“……”
那两封信确然称不上是正儿八经地传信,一封是告诉他王圣手可用,一封是告诫他在宫外小心。虽然有羽卫帮忙通信,但到底怕谢杨察觉,又担心走漏风声,是以信中留字寥寥,又格外深奥。
饶是谢祁,当时也是揣摩多时才看明白他的意思。
和给骆修文清晰易懂的留书比,着实相距甚远。
江怀允不自在地移开视线,委婉道:“先前你写给我的信,大多已经遗失了。”
换言之,就算他同意回字,也无信可用。
谢祁总不能当场写出来要他回吧?
这般想着,谢祁忽然笑吟吟道:“无妨。”
他笑意盈盈,怎么看都像是胸有成竹。
江怀允警惕顿生,还没来得及出声,便听到谢祁慢条斯理地叙述:“阿允在宫里那段时日,我在书房找东西时,偶然间将过往的那些书信都寻了出来。”
顿了顿,他故意调侃道:“说来也巧,阿允遗失的书信都遗失在了同一处,倒省去了我许多功夫。”
江怀允:“……”
谢祁噙着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须臾,视线定格在某处,笑道:“阿允耳尖红了。”
“……”江怀允搁下手中的书,淡然的语气中难得带了些许赧然,“你还要不要我回字?”
谢祁见好就收,并不恋战。
听到江怀允松口,忙在过往的书信寻出来一一摆在桌案上,善解人意地在一旁研磨,主动将笔递到江怀允手里,很是贴心周到。
江怀允:“……”
谢祁笑容满面,兴致盎然。江怀允觑他一眼,顺从地接过笔,蘸墨,绷着脸在信件上运笔如飞。写就,便将纸张移开,去写下一张。
谢祁好奇,凝目去看,信件上整整齐齐地写着:
阅。
与偕留字。
字迹清晰,骨架分明,霎是好看。
谢祁津津有味地品评半晌,颇觉好笑道:“阿允就回我个‘阅’字,是不是太过敷衍了些?”
江怀允面无表情地抬眼,没说话,但所有的意思都藏在眼角眉梢:
——若要他继续留字,就噤声。
谢祁心领神会,识趣地比了个噤声的动作,再不出声打扰,只眼神带笑地看着他绷着脸写“阅”字,深觉有趣。
他们之间来往的信件不多,单字并不难写,没一会儿江怀允就回完了大半。
谢祁本就是看他整日闷着,才想了个由头逗他解闷儿,并非一定要他正儿八经地回信。
是以一个人回字,一个人研磨,书房中倒也分外和谐。
半晌,江怀允写字的动作倏然一顿。
谢祁研磨的间隙抬眼:“写完了?”
江怀允没有搭腔,只是抬眸觑他一眼,尔后提笔蘸墨,在纸张上落笔。
看笔画,似乎不像是“阅”字。
谢祁沉吟片刻,绕到他身后去看。
这封信是他去岁前往梓州时写给阿允的,那时他将将表意,唯恐阿允不眷红尘,特意留书给他,循循善诱地叙说着尘世的美好。告诉他,尘世不仅有谢祁,还有更多数不胜数的美景妙境。
而如今,那封信件的空白处,正被崭新的笔墨填充。
江怀允行云流水地写:
纵得蓬莱仙者寿,
何胜人间有白头。
他曾告诉他尘世美景万千,诱引他敞开心扉去接纳。
他却回应他,世间种种,都抵不上同谢祁的白头之约。
谢祁心绪起伏,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行字,久久未动。
这是最后一封信。
江怀允大功告成,也不去看谢祁的神情,径直放下笔,准备起身。
谁料刚一动作,双手便被人扣在圈椅的扶手上,紧接着,谢祁俯身,阴影正好将方寸之地拢个完全。
手腕被桎梏在硬邦邦的扶手上,咯得微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