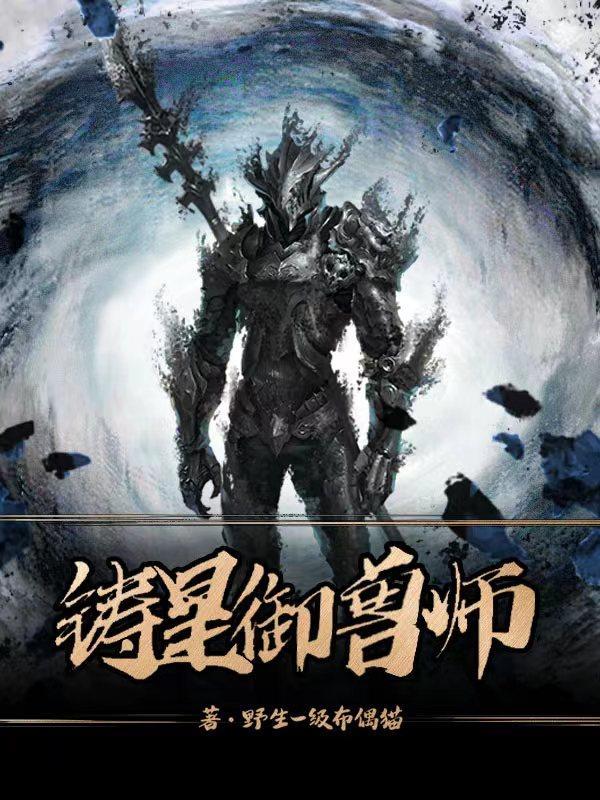车臣小说>归途电视剧 > 分卷阅读25(第1页)
分卷阅读25(第1页)
礼,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一直这样对待自己。
他唯一冲破禁忌,就是当年最年轻气盛、最按捺不住那份血气方刚时,和那个人在背人的角落里偷偷互撸,他们接吻,激烈地去解对方的武装带,去摩挲对方的身体,可不管每次再怎么情急,对方再怎么一边用力吻他,一边拉着他的手往自己身后送,陈照来始终不肯,他揽着对方的腰给对方打出来,在对方靠在他怀里喘着粗气时低声说:不着急,现在先不着急做,我们以后还很长……
他忘了不是谁都会为这个“以后”、为这个“很长”而悸动。
所以他被扔掉了。
他有过太多遗憾,太多无从弥补,于是他的心一点一点冷下来,不再期待。
可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陶东岭呢……
陶东岭是他另一个遗憾吗?
不是吗?
陈照来闭着眼睛缓了一会儿,掀开薄毯趿着拖鞋进了洗手间。
他没开灯,低着头一手撑墙,一手往下伸去……
曾经克制不是不敢,是不想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他想坦坦荡荡面对感情。后来克制是因为心里没有人了,淡了,冷了,而现在……
陈照来想,算了……他也会疲惫,他此刻再也提不起那股毅力,去赶走脑海里那个影子、那片丘陵起伏的小麦色,那张脸笑得耀眼,陈照来躲无可躲,无力抵挡,他不想挣扎了,就这一次,他重重呼吸着,抚弄着自己,在心里说,就这一次,想着那张带酒窝的脸,弄一次……
陶东岭第二天打电话时无人接听,他一口气打到第三个,陈照来才接起来,一边接一边还在跟旁边人说话。
“来哥,你忙着呢?”
陈照来“嗯”了一声,走到了个安静的地方。
陶东岭问:“才十点多就这么忙了?我听着你那边好些人说话呢。”
陈照来说:“昨晚半夜下了场暴雨,响云沟那边公路被水冲了,这边滞留了不少车。”
“啊?”陶东岭一愣:“这么严重?路冲断了吗?那得多久才修好?”
响云沟是陶东岭常走的路线,离陈照来这儿往北三四十里,那一段儿地势确实挺操心的,两边都是山,因为地质不太稳定,有关部门还专门在那设了地质监测点。
“没断,就是山上冲下来的砂石淤积,等水退了路政清理一下就能通开了。”
这边靠山,绕路一样不好走,很多司机都停下来等着水退,沿途饭店的院子里门前公路边都停满了车。
吃饭的人多,陈照来把这几天学校放假的陈鹏叫来帮忙,二婶也来了。二叔这几年虽然一直生着陈照来的气,但每回店里忙,二婶过来帮把手,他也从不拦着,就是个嘴硬,在陈照来的个人问题上死活不松口,二婶跟他不知吵了多少回了,到底谁也没吵赢谁。
三个人忙前忙后,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响云沟那段路清淤完成,地质部门勘探后认为后续生次生险情的可能性很小,便解除了封禁,很多司机抓紧时间上了路。
陈鹏和二婶晚上没回去,在店里住下了,吃饭的时候陈鹏眼睛一直瞄陈照来,一脸有话想问的样子,陈照来没搭理他。
吃完饭上楼休息,陈照来脚刚进屋,门还没等带上,陶东岭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陈照来接起来说:“你这干嘛呢,一天三顿电话追着打。”
陶东岭说:“咋的了啊,我这都挑你不忙的时候了。”
陈照来无奈:“我怎么不忙?你天天就没别的事儿干吗?好不容易闲几天,跟朋友出去喝喝酒打打牌不好么?”
陶东岭的床听着就不怎么舒服,一翻身“咯吱咯吱”响,他那边“咯吱”了几声,说:“我不喝酒,常年开车这点儿觉悟还没有么?再说……我酒量又不好……”
声音越说越小,陈照来靠在门上,忽然笑了笑。
“有多不好?”他问:“沾酒就倒?”
“那也不至于,”陶东岭认真说:“怎么也得两三杯吧,两三杯差不多。”
“白的?”陈照来低头咬了颗烟出来,点着火,含糊不清地说:“那也得看度数,三十来度和五十来度的两三杯可不一样。”
陶东岭那头顿了顿,说:“啤的……”
陈照来尽量忍着了,但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