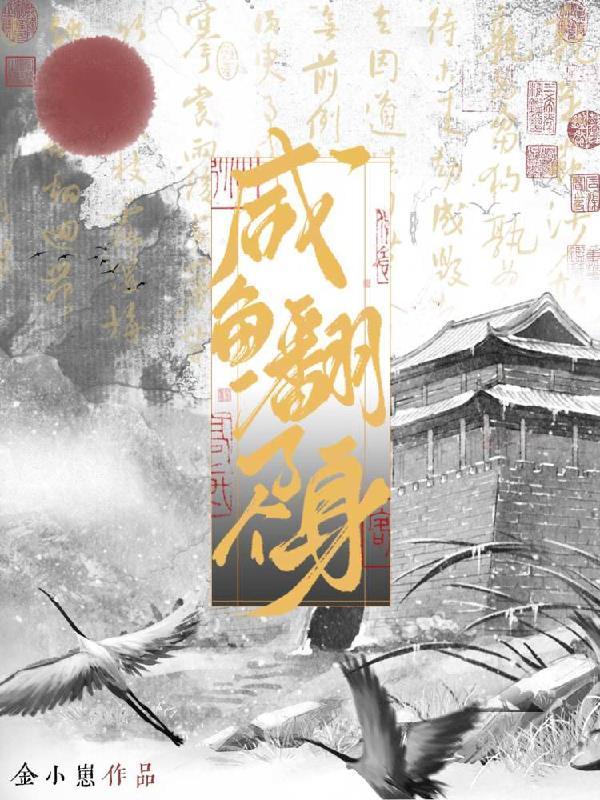车臣小说>人鱼的诅咒俄语歌曲中文谐音 > 第33章(第3页)
第33章(第3页)
像砺石在因摩擦而损伤,清晰可闻地,那嗓音在随着字句的增多而嘶哑下去。
但声音没有停止:“……领地,是名字。”
随后它仰起脸,将蹼掌里的手慢慢往窗框内再度拉进一寸,等候他的下一句。
带着这种徘徊在失声边缘的嗓音,自始至终,那都是一种格外专注于交谈的模样,那称得上津津有味的专注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人类才是在交代未知秘闻的那一个,才是开口说话会令人感到纳罕的那一个。
低下头,艾格看去自己被拉入窗内的手,那只蹼掌托着手背,湿润的指头避着伤痂扣着掌心,一个紧紧的、却怪异而不得其法的交握。
他感到手指在因长久未动而泛起一点麻意。
触碰一只兽类的手爪是一回事,与一个交谈对象握手又是另一回事。看了一会儿,他抬起手指,照着正常的握手方式,反手扣去了那只蹼掌。
人鱼低头看去,阴影里的鳃尖颤了颤。
掌心贴上掌心,虎口嵌入虎口,停顿片刻,他力度适中地握了握,最湿润的部分是它指间的蹼。
“萨克兰德。”松开手指,抽回手,他想起那座岛屿与这艘船相隔的海域,“这么说,你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没等手抽回窗外,人鱼蹼掌前伸,再度握了上来。
它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一点一点地将那只始终放松的手掌重又拉回窗框,拉到身前。
再开口时,那喉咙像某种堆满青苔的蚌壳在被艰难撬开,“……很远。”它说。偏过头,停顿片刻,它似乎也在倾听自己的声音,可这已经是失去声音的一句,喉咙滑动数次,“海上……总是很远。”
又是几乎无声的一句。
艾格视线下移,从它时不时滚动的咽喉,望去胸膛上的那道伤。
“看得出来,一路上危险还不少。”一时间,他想不到海里有哪种危险会损伤着这种动物的嗓子,误食了什么东西?有异物卡在那里?这样想着,他伸出另一只手摸向了眼前的喉颈。
人鱼注视着那只碰来咽喉的手,规律扇动的长鳃慢慢贴到脑后。
手底下喉骨完整分明,没有任何异样。咽喉的伤本就肉眼无法看见。
“有东西卡在这里?”艾格问。
人鱼的喉咙再度酝酿起一点震动,应声的话从胸膛来到嘴边,它张开嘴。
没等那嘶哑之音再次出现,艾格抬了抬手,把手背上的下巴合了上去,“点头,或者摇头。”
于是人鱼闭上嘴,摇摇头。
很难说清它的注意力是否在这句问话上,它一边摇头,视线却始终跟随着那只从眼前收回的手。
“知道自己喉咙受伤的原因吗?”
停在手上的视线来到他的眼睛,这回它像是思索了片刻,再度摇了摇头。
艾格不再询问了。
越过它的顶,他看去它背后黑漆漆的舱室。
油灯已经在里面燃尽,若隐若现的海水气味从内飘来,那是海上无处不在的一种气味,理所当然地充斥在轮船每一个角落。
短短半个夜晚,这间大船管理者的舱室已然成为了这条动物的地盘。
无论它几次三番赖着这条船有什么目的,但此时此刻,对于这条浑身挂伤的动物来说,比起需要用爪牙搏斗的海底,也许这艘被恐惧统治的人类轮船才是它最从容来去的场所。
只要他对它鸠占鹊巢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艾格看向那截回归沉默的喉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