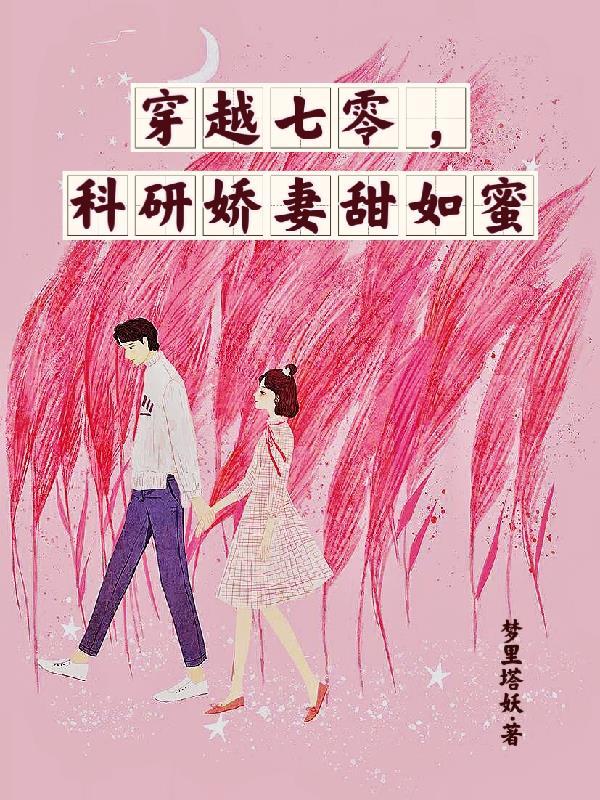车臣小说>古典制约和操作制约的区别 > 第 3 章(第2页)
第 3 章(第2页)
第二天早上直接上吐下泻烧到三十九度。
连他亲爸亲妈都来了。
燕家跟牧家算世交,两边家长稍微客气两句,直接在燕知床边围了一圈。
支璐有些不好意思,“这孩子身体随我,总生病也是添麻烦。我跟珵哥商量了一下,要不等他升了初三,我们就把他送出去锻炼锻炼。”
“那你问牧长觉吧,”海棠被她逗笑了,“你儿子的事儿,现在都是我儿子在管。我跟牧如泓一点手插不进去。而且我看你们两口子,也未必做得了主。”
躺在床上输着液,燕知扭头看牧长觉。
他非常信任牧长觉。
支璐要送他出国,牧长觉怎么可能同意?
他一定会有理有据地说服所有人:天天身体不好,从小没离开过他,不能出国。有时候又看不见东西,一个人不方便。
不让燕知走,理由可太多了。
而且牧长觉冷静自持,虽然只比他大五岁,在哪说话都是有分量的。
可能烧得糊涂了,燕知听不清牧长觉说了什么。
然后突然进来几个陌生人,抬着他的床就要出门。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燕知惊恐地从床上爬起来。
“送你出国。”
护照上“燕征天”三个字,醒目得刺眼。
那是他从前的名字。
年少的燕知挣扎着往回跑,一边哭一边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也不生病了,你别送我走。”
但是不管他怎么跑,都好像迷失在一场大雾里。
直到燕知在一身黏腻的冷汗中惊醒。
昏暗的光线,安静的房间。
“醒了?”身边的人问他。
燕知有点茫然地转头,缓缓聚焦打量他。
牧长觉一身亚麻衬衫休闲裤,弯腰单手拄着膝盖,轻轻拨他的刘海,“做噩梦了?”
燕知愣了几秒,慢慢向上伸手,用尽全力停留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
好像这样就可以真的紧紧搂住一个幻象。
这是他的牧长觉。
他不惜一切分离出来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浮木。
每当他即将溺水时,永不缺席的救赎。
“梦见什么了?”牧长觉轻声问他。
“梦见小时候我爸妈要送我出国,问你意见。”燕知把脸埋在他肩窝里,闷声闷气地说。
“那你还记得我当时怎么说的吗?”牧长觉在揉他的后颈。
燕知有点赌气,“不记得。”
“那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啊。”牧长觉收起声音里的笑意,“我说除非我死了,不然天天不能走。”
“中二病。”燕知终于笑了。
“那时候我也才十七啊,”牧长觉亲了他的耳朵尖一下,“我说得不好,让你不高兴了?”
燕知还是忍不住委屈,“那时候你都不喜欢我,我走了你不刚好清净?”
牧长觉把他松开一点,半笑不笑地看着他,“燕天天,你良心呢?”
“喂狗吃了。”燕知噩梦刚醒,心情很糟。
尤其跟眼前这个人,他从不掩饰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