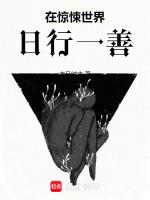车臣小说>肉身莲制作过程 > 9(第5页)
9(第5页)
白湫廉是个一诺千金的人,说要好好照顾梁清也,就必然要做到做好。白湫廉雷打不动一天来三次送饭。早上五点半多买好饭,轻手轻脚放在床头柜上,不吵醒还在熟睡的梁清也。医院离学校有一截儿距离,白湫廉一出来医院门立马狂奔去赶公交。
中午休息时间不长,要是撞上了放学大部队更是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出了大门了。学校里头老师多少都知道白湫廉和梁家那小太子有点儿不清不楚的关系的,往日里只要不是太出格的行为大多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白湫廉毫不手软,直接狐假虎威耍特权,最后一节课翘掉去医院给梁清也打饭,下午再踩着点儿上课。
白湫廉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从小到大午休习惯了。虽说来了南边儿吧人家们没这习惯,但他还是会硬从缝儿里挤出点儿时间中午睡上一觉的。但照顾梁清也这段时间,白湫廉每次去医院路上一来一回耗掉不少时间,而且回程公交车上他也不敢睡,生怕坐过了站。早上起的早晚上睡的迟,中午也没时间小憩片刻恢复精力,这导致他下午第一节课必然是昏昏欲睡。
早上误一节,有时候累得不行睡一早上也是常事,下午又误一节,积少成多,白湫廉又不是顶聪明的学生,现在年级第一的成绩是他拼老命换来的。在这段操劳日子里的第一次月考,毫不意外他掉到了年级五十名。本来白湫廉还无所谓,但这下可好,找他代写作业的单子一下子少了一半儿。气得他有一天晚上给梁清也掰好筷子后,转身就躲到厕所里大哭了一场。
白湫廉怕梁清也多想,哭得极为克制。谁成想这医院的单人病房隔音并不好,白湫廉骂了自己多久梁清也就清清楚楚听了多久。
“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梁清也看着不停地吸溜鼻涕、眼睛哭得红肿的白湫廉,男孩儿出来之前可是好好洗了把脸,结果哭得太狠,这杯水车薪的凉水根本毫无用处。
梁清也知道是自己拖累了男孩儿的学业,自厌的同时也被白湫廉的泪水引得想哭。她又要被当作累赘推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心里酸涩不已,暴戾的情绪又蹿到心头,诱惑她去用床头白湫廉给她带饭用的保温杯,把他砸个头破血流,惩罚他的始乱终弃。
梁清也的指甲焦躁地扣着被子底下的床单儿,深深呼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狂躁的情绪开口道:“我会自己掏钱找个护工,不和梁济说,你还能拿到钱。”
晚上白湫廉是不走的,就将就在旁边的折叠床上陪梁清也一晚上,随时照应。梁清也不愿意穿纸尿裤,也拒绝使用尿壶。有时候她喝得水多了,难免起夜次数会多一些。白湫廉为了照顾她精神常是紧绷的,又在陌生的环境,睡眠轻了不少,有时候梁清也起身动作带起来的细微摩擦声都会把他给惊醒。
睡眠不足又操劳,是个人都会精神衰弱。但尽管如此,白湫廉也从来没给梁清也耍过一丁点儿脸色、埋冤指责过一句。他只会在梁清也再一次在半夜吵醒他时,露出一个萎靡不振的笑容,打个哈欠迷迷糊糊摸索过一边儿的绷带缓慢地缠好在自己眼睛上,小心翼翼地走到梁清也身边儿来。
有会梁济找白湫廉交代事儿的时候顺带看望一下梁清也,一推门就见梁清也搀扶住蒙眼的白湫廉慢慢挪动到厕所。
梁济皱了皱眉头,训斥道:“梁清也,你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穿个纸尿裤会死吗?你是非要等崩了线就开心了,不想出院了?非要这样折腾人。”
梁清也温顺地低下头,恭敬地听着梁济的训骂。或许是这几天和温柔包容的人待久了,忘了自己早就不配有可以任性的资格了。她正要开口应下,就被白湫廉打断了话头。
“这是啥话,一点儿都不折腾,两秒钟的事儿能有多麻烦,”白湫廉狗腿地凑到梁济跟前,打哈哈道,“梁哥消消气儿嘛,是我硬不让姐姐穿纸尿裤的。穿那玩意儿干嘛呢,鼓鼓囊囊一团捂得多不舒服嘞,更何况这大夏天热得起痱子咋办?”
“让你说话了吗?”梁济抬眼看了一眼在一边儿急得团团转转的白湫廉,一股子闷气憋在胸膛。明明是在替这瘦猴儿说话,怎么这么不识好歹?梁济惯不是个能忍耐的人,直接抬脚故意踩到白湫廉那条坏胳膊上,把人踹翻在地。
白湫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人仰马翻仰倒在地上头了,肩膀传来的疼痛紧随而来,他面上死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眼泪狼狈流下,心里头已经泪流满面了。这下好了好不容易缝好的线又让这傻逼给踹开了,一会儿又得挨针了!操他妈的!
白湫廉真是想狠啐一口,这阴晴不定的货色咋不讲武德突然发难,但到了嘴边儿又是彻彻底底变成了另一个样儿:“梁哥教训的好!看我这嘴贱的,插什么话!踹得好!”
“这么喜欢赚钱吗?”梁济背光面朝他,居高临下地看着白湫廉,脸上的表情让他捉摸不透。
“必须的!”白湫廉心里有翻了个白眼,问出这话脑子多少有点儿病,要是不爱钱,谁会上赶着当街流子?但这话似乎说得不中听的很,白湫廉赶快又补上一句:“唉,但主要还是喜欢在梁哥您手下干活的快乐啊!誓死效忠龙帮!”
“是吗?”梁济被这话逗乐了,睨了一眼坐在床上低着头不发一言的梁清也,从裤兜儿里掏出皮夹,数了数里头的钱,没几张,但都是外钞。
梁济把里头大面额的钞票点出来夹在指缝间,玩味的朝白湫廉说:“你不是喜欢钱吗?来,现在跪着像狗一样爬过来,再叫两声,这几张美钞全是你的了。”
梁清也听见这话,狠狠攥紧手下的棉被,她几欲要开口好好辱骂梁济一番,可这话到嘴边儿是怎么也吐不出,她可悲的发现,她仍旧是那个逆来顺受的胆小鬼罢了。
“哎,好嘞!”白湫廉还屁股坐在地上,一听这话犹豫不过三秒就是应下,双眼泛光地死盯梁济指尖儿的钞票。他眼神老好了,眯起眼睛数了数。靠居然有八张,看头像约莫是百元大钞,而且现在汇率还是一比八。对不起了梁狗,你要当这个冤大头他白湫廉就不客气地趁人之危了!
白湫廉一个翻身正面朝下,先是支棱起两个膝盖,然后再曲起好胳膊的关节支在地上,坏的那条因为刚受了伤使不上劲儿,只好耷拉在地上拖着走。因为就三条腿供白湫廉趴,再加上还得小心不能压着一条胳膊,他爬得摇摇晃晃,爬得艰难又缓慢。
梁清也从未感受过如此难熬狠戾的酷刑,每一秒的无限延长,她克制不住去看在地上像条毫无尊严的狗一般爬行的男孩儿。她看男孩儿因疼痛冒冷汗的额头,看他强忍不适而咬紧的牙关。分明受辱受刑的不是她,她为何会感到一条虚无的绳索勒紧了她的脖颈要置她于死地?
总算爬到了梁济脚边儿,白湫廉乖巧地跪着,毫无心理负担地汪汪叫了两声,眼睛一直如狼似虎盯紧梁济手里的美钞,恨不得立马就化作恶犬叼嘴里头。
“嘁。”梁济冷笑一声,对着白湫廉的脸扔下了美钞,没砸中,但却不偏不倚掉在了白湫廉裤裆的位置。
白湫廉也没想太多,反正梁狗时不时就抽一下风,喜滋滋地拿起掉裤裆钱揣兜里,余光瞥见梁济要走,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给人送到了门口。
“为什么……”梁清也心绪复杂,斟酌再三对着跷二郎腿坐椅子上乐呵呵数钱的白湫廉询问道,“要维护我?”其实她更想问,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尊严踩在脚底下,她既怕戳到了痛楚,又怕听到害怕的答案,所以最终话到嘴边还是拐了弯儿。
“本来就是啊,穿着多不舒服,而且心里头也过不去那道坎儿吧。”白湫廉一点儿没尝出梁清也沙哑的嗓音里潜藏了多少波澜,没心没肺地应着。
“我以前皮的很,膝盖骨错位过。腿瘸了去学校不方便上厕所,活人又不能让尿憋死,我自然是不乐意,觉得这么大的人了穿这不让人笑话死,但他们还是强迫我穿纸尿裤喽。那玩意儿鼓囊一大块儿,套上裤子也明显的很,我坐轮椅上头被推进去的时候真不想站起来坐到椅子上,就这两秒钟我都生怕被人看出来。其实我当时真的宁愿被尿憋死也不想这么耻辱哈哈。”白湫廉抖着腿漫不经心地说,“实在憋不行了,我强逼着自己坐在教室椅子上头尿,好家伙一股热流直接浸湿了全部,甚至都到屁股后头了!那玩意儿吸水是真不行,你妈还侧漏湿了我一裤子。趁着大课间他们出去耍,我站起来拽着裤子屁股那一块儿使劲抖,就想着赶紧干、赶快散散味儿别让人发现我尿了一裤子。那时候是真想一头撞死啊,我羞得都快涕泗横流了!所以我大概不自量力是能懂一些姐姐你的心情的,疼就疼一点儿,麻烦不怕有我在,不穿就是不穿了又能怎样?”
日后再回想起来那一天,似乎这就是梁清也日暮途穷的开始;那一番话再没有人对她说过,似乎这就是她万劫不复的。
“姐姐,对不起,”白湫廉失落地耷拉着脑袋,“让你误会了,我这就是到了日子该发疯了,和你没一点关系。”白湫廉揉揉眼睛,也不多狡辩,只是委屈巴巴地说:“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啊?真对不起啊姐姐,姐姐和梁哥说换人吧,今儿还再委屈下我再搭照一天,明天来了新的人我再走。”
梁清也不敢去看白湫廉的眼睛,她无法面对着阳光的每日汇聚而成的那面墙,那上面她不同的面孔互相重叠,互相连接,如苍白而沉重的巨大花朵,顽固地被替代,死去。
梁清也无意识地摸了摸耳朵上耳洞的茶叶梗,被她报复似戳出孔洞的皮肉在恢复的日夜里没有一丝一毫病变发炎的迹象。
在恢复意识的第一夜里,梁清也躺在床上,心里想得太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还在脑海布局着之后的暗杀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三皇子计划,就听见一阵衣服摩擦声。
梁清也条件反射地调整呼吸放缓呼吸,伪装出一副熟睡的模样,趁其不备反击。这个屋子里只有她和白湫廉两个人,他要干什么,是这么多天终于露出马脚了吗?他是要杀了自己吗?一想到这个可怖的可能性,窒息感犹如厚重的水面,紧紧地包裹着梁清也喉咙,无法呼吸,每一次的挣扎都像是试图在泥潭中挣脱束缚。
屏息凝神好一阵,梁清也抛弃了毕生所学的一切反击技巧,她想等一等,再等一等,等到那把刀完完全全贴上她的脖颈再暴起,然后杀死白湫廉,顺便杀死那个正常人的梁清也。
倏忽间,火辣辣的耳垂传来一阵冰凉,有什么东西戳刺在上面,但那动作极为轻柔,梁清也几乎没感觉到什么痛感。她原以为这就是所有,静待几秒,耳垂又传来丝丝缕缕的痛。
一只手温柔地捏住了自己的耳垂,那人离得是极近的,呼出的热气全部喷洒在自己发间,引得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人把什么东西捅进了还肿胀的耳洞里,来回左右试探想要穿过去。耳垂上估摸是有什么穴位吧,被这么一捣鼓梁清也有些头晕目眩和反胃恶心。那人真是耐心到了极点,不愿粗鲁地直接捅穿烂肉穿过去茶叶梗,轻轻柔柔地反复试探,势要把不适疼痛降到最低。
“呼。”那人长出一口气,总算把那小棍儿卡在耳洞里头了。这还没完,梁清也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耳朵又是一烫,里里外外被擦了个遍,那人才算罢休。
等到有一个人绵长的鼻息徘徊在屋里,梁清也眼角那滴要落不落的泪水才终于顺着眼角滑进发丝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留下吧,”梁清也轻轻摩挲着耳垂。人都是自私的,她自然不能免俗,“继续照顾我吧,白湫廉。”
或许此时还算天真的梁清也不会想到,日后躺倒在码头上的她,会因为这简单一句话而顿时亮晶晶的、难以忘怀的眼眸而悔不当初吧。或许她就算未卜先知,也会甘之若饴。
“怎么突然想起这些个陈年烂谷子的事了。”梁清也从口袋摸出烟,叼在嘴里点了一根。她自嘲地想,真是虚伪啊,梁济的走狗梁清也,到头来,把白湫廉推进泥沼的不也有她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