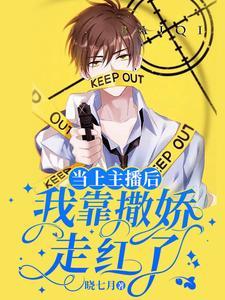车臣小说>新新女驸马百度资源 > 60第六十一章 同来望月知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第3页)
60第六十一章 同来望月知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第3页)
慢行了两日,冯素贞在马车的晃动中从小憩中醒来,夏末的凉风掠起了马车窗口的帘布,她从那窗口里望见了熟悉的夏日浓阴。
去岁此时,她也是如此慢行在京西的路上,身后的骑驴少女声如银铃地给她讲着朝堂皇室里的种种秘辛。
她静静坐起身来,端详着窗外的风光,渐渐看到了怀来熟悉的城墙。
静谧之中,车前有聒噪声传来——
“你看着,就城楼上面左数第三个垛口,我去年就在那儿砍了三十四个鞑子下去!”
“真的?就你这小身板儿?有那么厉害?”
“嗬,这算什么,若不是我用的刀不好,卷了刃,砍他个百八十个不成问题!”
听着梅竹啧啧的惊叹声,冯素贞隔着车帘凉凉道:“怀来南北夹山,而鞑子自西来,若是怀来东门一个垛口能爬上三十四个鞑子,那京城早就满城鞑虏了。”
车前的声音静了片刻,没一会儿就又响了起来:“没错没错,我当时砍鞑子砍得太累,都不辨东西了!等咱们到了西门,我再指给你看啊!”
冯素贞笑了笑,没再去揭破,侧身倚在窗口虚眼望向怀来的城楼。
斯人不知何处去,城垣依旧笑东风。
“小姐,前头又有做法事的,可要去舍些银子?”前头忽然传来了梅竹的声音。
冯素贞掀开帘子对着梅竹轻轻点了点头。
一路西行,沿途常常能看到和尚在做法事。自欲仙帮倒了,北地信佛的人便好了好些。
距去岁鞑虏侵入已历一载,这做法事的都是一些幸存的灾民在悼念往生的亲眷。冯素贞心肠软,每每见到,都会下车去凭吊一番。
如此又慢行了两三日,便到了宣大总督如今的行营驻地。
二十万虎狼之师驻扎于此,行营绵延逾百里,却是井井有条,军纪昌明。冯素贞曾在怀来卫里待过阵子,深知打仗不易,治军更难,见此情况心里已有了几分敬服之心。
故而当和顾承恩在辕门外初见时,虽见其人身量不高,长相和气,丝毫看不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气息,冯素贞也丝毫不敢对其小觑。
众人走过一片练阵的行伍,冯素贞眼见得十数种兵器长长短短变换组合,却是丝毫不乱,不禁赞了句:“好儿郎!顾帅,这是什么阵法?”
顾承恩照实答道:“此是仿着戚家军的鸳鸯阵琢磨的并蒂阵。”
冯素贞沉吟道:“此阵我曾听闻,长短兵器搭配无间,机动灵活,拆开即可变阵。纵然是被冲散了,也不至于陷入被动,最是适合山地丘陵。”
顾承恩哈哈笑道:“早闻冯大人是文武全才,果然见识过人。这并蒂阵拆分开来是鸳鸯阵,再拆开,便是三才阵。”
走过这片练阵的队伍,迎面瞧见一众农人装扮的行人各自持着农具箩筐从营地旁的田地里走出来。
虽是农人装扮,但那些人腰背挺直,步履不乱,冯素贞便明白,这定然是屯田的官军。
果然,顾承恩笑着解释道:“冯大人来得正好,今日恰收了一波新鲜菜蔬,晚上可得好生尝尝我宣大军中自己种的伙食。”
众人复又前行,待经过了数个演兵的校场之后,已然行走了数里路,冯素贞有些不支,正想着休息片刻,却见到了个特立独行的练阵队伍:阵前一人将手里的长剑舞得密不透风,一片金光剑影晃得人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形,而其后的数十人则翼展开来,中部却如箭镞一般,跟着那人缓缓前行。
冯素贞皱了皱眉:“顾帅,这是个什么阵型?莫不是靠着为的那人破军前行?”
顾承恩大笑几声,高声唤道:“严守备!”
随着这一声唤,那片剑影瞬时破开,为那人腾空跃起,在空中几经翻转,如若御风而来,翩然落在众人面前。
冯素贞早在那声“严守备”喊出,心里就有了数,但看清来人的面容之后,仍是有些吃惊。
来人当然是一剑飘红,除了他,军中怎能有如此一夫当关的剑术?
那个昔日冷漠不羁的剑客虽依旧神色淡淡,却不再如杀神降世那般令人不能直视,他束着利落的髻,依旧坚毅的轮廓里带了几分落地成人的烟火气。
他大步近前,拱手行了个礼,却一声不吭。
顾承恩笑着上前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道:“严守备剑术高格,有一夫当关之势,此阵是我特意为他所制。”
冯素贞叹服不已,上前寒暄道:“严兄已经升了守备?”她记得去岁天香还说是个百户。
严凛泓点了点头。
“严兄在顾帅麾下,过得可还习惯?”
严凛泓又点了点头。
“……若是她知道,定然很开心。”
严凛泓眼中闪过一瞬间的光亮,他——还是点了点头。
这不爱说话的性子倒是和以前一个样。
顾承恩心知照这个情况,两人“叙旧”是叙不起来的,打着圆场道:“此处已经是中军帐,冯大人的营帐就在一旁。冯大人定然是累了,不妨歇息片刻,待到了晚上,顾某人再为冯大人接风洗尘!”
冯素贞求之不得,自是欣然从命。
进了帐,单世文帮着梅竹摆放冯素贞的用具,忽地自言自语道:“他真有那么厉害吗?”
冯素贞耳力灵敏,不禁问道:“谁?”
“顾帅。”单世文抬起头来,“我大哥少有服气的人,顾帅便是其中顶尖的那个。可我却觉得,他这人一身官气,却不像个将军。论气势,还不如东方胜呢!他穿着戎装还好,若是脱了戎装,怕是会被人当成个落魄书生。”
冯素贞摇摇头道:“人不可貌相,我觉得,他和东方胜是两种人,兴许,日后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