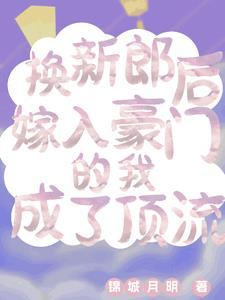车臣小说>春闺杀结局 > 第40章 欺瞒(第1页)
第40章 欺瞒(第1页)
御书房外,青甲禁军规整肃穆的列在台阶下,犹如两排古树。
殿内一片寂静,太监垂首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帝王的吩咐。
青釉狻猊香炉静静散着青烟,烟细如线,在阳光中渐渐消散。
沈珏收回目光,修长漂亮的手指轻夹起一枚黑子,落定。
嘉文帝失笑,无奈的点了点沈珏,“你又给朕下套。”
沈珏,“陛下大局已定,臣这点伎俩,入不得陛下的圣目。”
嘉文帝又观了观棋局,沈珏的狡黠就在于,他让你胜,却是惨胜的场面。
对于嘉文帝来说,牺牲大片的棋子才获得的胜利,实在算不得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但白子还是落在了沈珏预留的那处空地。
帝王眼里只有胜,没有退,即便境况凄惨。
“陛下赢了。”沈珏道,略抬了抬手,立侍的小太监就奉上茶来。
嘉文帝却仍端详棋局,一步一步复盘,才发现沈珏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挫伤,而非赢,抛开胜败,沈珏可以从心所欲的大环套小环,各种烟雾弹的迷惑他。
“满朝文武,只有和你下棋,朕赢得如此憋屈。”嘉文帝接过太监捧上来的龙井,啜饮了好几口,方放回太监手中。
他看向面前芝兰玉树的沈珏,面容与他最疼爱的胞妹荣阳长公主有六分相似。
窗外的梧桐树传来一阵蝉鸣,嘉文帝道:“入夏了,你母亲的生辰也快到了。”
“朕没记错的话,荣阳今年正四十。”
一旁的太监忙答,“陛下好记性,长公主今岁正是四十。”
嘉文帝的手无意识的在膝盖上拍了几下,颇有些感慨,“真是白驹过隙,一转眼荣阳都四十了。”
“朕还记得,荣阳嫁给沈国公时,才十八,一个倾国貌,一个万胜将。”
嘉文帝想到沈国公,顿了顿,转向沈珏:“你母亲的生辰,你觉得朕应当如何为她操办?”
嘉文帝与沈珏向来喜欢以长辈自居,说话间大多慈善温和的,普天之下,得此待遇得,除了沈珏,便是嘉文帝最喜欢的四皇子了。
——————等我几分钟,就十分钟就够了——
沈江骊,重丘县县令千金。
她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在父母宠溺下长大,本以为一生平安顺遂,十岁那年,父亲为锦绣前程,将母亲转送于高官为妾。
从云端坠落,沈江骊爬出泥淖,孤身入京。
所有人都将母亲当棋,用而弃之;她却要,把母亲带走,带出那座金笼……
只是权势滔天的国公府中,孤立无援,稍有不慎便会被碾为灰烬。
风流浪荡的沈四,佛口蛇心的老夫人,将她视作眼中钉的沈二夫人……
沈江骊步步筹谋。
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沈江骊带着母亲远走高飞,日子过的逍遥。
本想着行商补贴点家用,不想踩在风口,一举成了皇商。
重返京都,又见故人。
沈珏立在梨花树下,苍白的细碎的梨花翩飞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他眸色晦暗,“原来,裴夫人……是你啊。”
听那语气,怨气冲天。
都说,女子这一生离不开男人。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沈江骊却坚持,靠山靠会倒,唯有自己才是永恒不变的依靠。
她心狠手辣,她冷心薄情。
孤狼一样守护她的母亲、朋友。
关于爱情,有过心动。
但她把那颗及膝高的枇杷树拔了,划破的掌心流血。
那时,沈珏并未察觉。
好在,并未察觉。